|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 家常、感情、文學、電影、時政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兩大巨擘──夏濟安、夏志清夏氏兄弟,18年的魚雁往返,是一代知識分子珍貴的時代縮影
現代中國學術史料的重大事件 ※ ※ ※ 按語(節錄) 濟安1916年生,長志清五歲,出生於一個中產之家,父親營商,曾任銀行經理。父母都是蘇州人,但在上海成長,他們還有一個幼妹,名玉瑛。抗戰時,濟安不肯留在上海,為日本人服務,隻身經西安,輾轉逃到昆明,進入西南聯大,擔任講員。勝利後,1947年隨校遷返北平,入北大西語系任教。抗戰時,志清與母親、幼妹留在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後,考入上海海關任職,1946年隨父執去臺灣港務局服務。濟安認為志清做個小公務員沒有前途,便攜弟北上。由於濟安的引薦,志清在北大做一名助教,得以參加李氏獎金 考試,志清有幸奪魁,榮獲獎金,引起「公憤」,落選者聯袂去校長辦公室抗議,聲稱此獎金應該給我們北大或西南聯大的畢業生,怎麼可以給一個上海來的「洋場惡少」?胡適雖不喜教會學校出身的學生,倒是秉公處理,尊重考試委員會的決定,把李氏獎金頒發給夏志清,志清得以赴美留學。胡適不肯寫信推薦志清去美國名校讀書。幸賴一位主考官,真立夫(Robert A. Jeliffe,原是奧柏林大學教授),建議志清去奧大就讀。志清1947年11月12日乘船駛美,十日後抵舊金山,轉奧柏林,發現奧柏林沒有適合自己的課程,去俄州甘比亞村(Cambier, Ohio)拜望新批評元老藍蓀(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教授,由藍蓀寫信給其任教耶魯的弟子勃羅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志清得以進耶魯大學英文系就讀,三年內便獲得英文系的博士,更於1961年出版了《近代中國小說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為中國現代文學在美國開闢了新天地,引起學者對現代文學的重視,不負濟安的提攜。 濟安不僅對志清呵護備至,更引以為榮,常常在他的朋友學生面前讚美志清,是以他的朋友都成了志清的好友,如胡士禎、宋奇、程靖宇(綏楚)。濟安過世時,他臺大的學生來美不久,尚在求學階段,濟安和志清的通信裡,對他們著墨不多。按照時間順序寫來,濟安認識胡世楨最早,他們是蘇州中學同學。胡世楨博聞強記,對中國的古詩詞,未必了解,卻能背誦如流,參加上海中學生會考時,便脫穎而出,獲得第一名,來美留學,專攻數學,在洛杉磯南加大任教,很早便當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幸愛妻早逝,一人帶著兩個孩子生活,很是辛苦。我1970年與志清路經洛杉磯,曾去看望過胡世楨,他價值六萬美金的房子,建在一個山坡上,這個山坡,已不是當年草木不生的土坡,而是一個樹影扶疏的幽徑。他的兩個男孩,大概十幾歲,都很有禮貌。濟安信裡寫了世楨與來自香港某交際花訂婚又解除婚約糗事,讀來令人噴飯。據說世楨的亡妻,霞裳,秀外慧中,是公認的美女。後來世楨追求的女子,也都相貌不凡,可惜沒有成功,最終娶到的妻子,看照片似乎資質平平,倒是賢淑本分,夫婦相守以終。 宋奇(1919-1996)是名戲劇家宋春舫(1982-1938)哲嗣,原在燕京大學讀書,因抗戰返滬入光華大學就讀,與夏濟安同學,常去看望濟安,因而與夏志清熟識。夏志清從小醉心西洋文學,很少閱讀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他寫《近代中國小說史》時,很多書都是宋奇寄給他的。宋奇特別推崇錢鍾書和張愛玲。錢鍾書學貫中西,精通多國語言,是公認的大學者。張愛玲是暢銷小說家。《小說史》裡,對二人的作品都有專章討論,推崇錢著《圍城》是中國最好的諷刺小說,張著《金鎖記》是中國最好的中篇小說。把錢張二人提升到現代文學經典作家的殿堂。志清1969年請到古根罕獎金,去遠東遊學半年,我隨志清去香港住了三個月,常去宋家做客,記得頓頓有一道醬瓜炒肉絲,非常好吃。宋奇曾在電懋影業公司任職,與許多明星有交往。志清想看玉女尤敏。宋奇特別請了尤敏和鄒文懷夫婦。當時尤敏已息影多年,嫁給富商高福球。尤敏膚色較黑,沒有電影裡美麗。宋夫人鄺文美,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中英文俱佳,也有譯作出版,但為人低調,把光環都給了夫婿。她和張愛玲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她倆因背景相似,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宋奇夫婦是張愛玲最信賴的朋友。宋奇善於理財,也替張愛玲經營錢財,張愛玲晚年,並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窮困潦倒,她身後留下240萬港幣。宋奇夫婦過世後,由他們的公子,宋以朗接管,在香港大學設立了張愛玲紀念獎學金,頒給港大學習文學科及人文學科的女生。 程靖宇(1916-1997),出生於湖南衡陽,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抗戰勝利,隨校遷返北平,繼續攻讀碩士,住沙灘紅樓,是夏濟安的好友,也與夏志清熟識,為人熱忱,頗能文墨,筆名金聖嘆、丁世武、一言堂等,著有《儒林清話》。此公不拘小節,「吃、喝、嫖」樣樣來,只是不「賭」。他在北平時,曾帶濟安去過妓院,他指導夏濟安怎樣去與女友接吻。1950年濟安初到香港時,程靖宇在崇基學院教書,後來如濟安所料,因生活浪漫,以賣文為生(見卷三,信件編號351第319頁)。我1970年在九龍中文大學宿舍住了三個月,程靖宇已脫離教育界,靠在小報上寫文章餬口。他追日本女星失敗,倒娶到一位年輕的日本太太,並育有子女各一,他每個星期都會來九龍看我們,請志清去餐館吃飯,有時也請志清去夜總會聽歌,他太太高橋咲子在旅行社工作,他們包了一輛巴士(bus),請我們遊覽香港,吃海鮮。盛情可感,雖然他請的客人,除了劉紹銘夫婦我都不認識。1978年中國大陸開放,程靖宇欲向志清借七千美元接濟大陸的弟弟,孰不知志清薪水微薄,奉養上海的父母妹妹,毫無積蓄,無錢可借,得罪了朋友。靖宇不再與我們來往。他1997年大去,我們不知,自然也無法對他的家人致上由衷的哀思。 我1961至1963年在柏克萊讀書,與夏濟安有數面之緣,在趙元任家,在小飯館Yee’s,在「中國中心」,多半是與洪越碧在一起。越碧(Beverly Hong-Fincher)是來自越南的僑生,濟安在臺大的學生,華大的同事。他們有很多話可說,濟安絕不會注意到平淡無奇的我,更想不到我會成為他的弟媳,在他身後,把他的書信公諸於世。發表他與弟弟的通信是志清的願望,志清生前發表過他與濟安的兩封信(《聯合報》,1988,2月7-9日)後,一直沒有時間重讀哥哥的舊信,2009年,志清因肺炎住院達半年之久,每天叫我把濟安的信帶到醫院,可惜體弱,精神不濟,未能卒讀。康復後,因雜事纏身,無法重讀哥哥的信,於是發表兄弟二人的通信便落在我的肩上。將六百多封信,輸入電腦是一個大工程,於是我向好友王德威教授求救。德威一面向我盛讚蘇州大學季進教授及他所領導的團隊,一面懇請季教授幫忙。季教授慨然應允,承擔下打字做注的重任。濟安與志清在信裡,除了談家事,也討論文學、電影、國事。他們經歷了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他們除了關心留在上海的父母及幼妹,更關心自己的志業與未來。兄弟二人都是英文系出身,醉心西洋文學,但也熟讀中國的傳統文學,信裡隨手拈來,點到為止。若沒有詳盡的注解,讀來費力乏味,只好放棄。但有了注解,讀來會興趣盎然,信裡有文學、電影、京劇,有親情,還有愛情。濟安雖終身未娶,但認為世界上最美麗的不是綺麗風景,而是「女人」。 我終於完成了志清的心願,出版了夏氏兄弟的信件,首先要感謝王德威教授的指導與推動。德威是好友劉紹銘的高足,但與志清並不認識。他來哥大也不是由於紹銘的引薦,而是志清看了他的文章,一次在西德的漢學會議裡,特去聆聽他的演說,看見他站在台上,一表人才,侃侃而談,玉樹凌風,滿腹珠璣,便決定請他來哥大接替自己的位置。志清有一次演講,稱請德威來是繼承哥大的優良傳統,「走馬薦諸葛」。原來志清來哥大是由於王際真教授的大力推薦。王教授原不認識志清,只因在耶魯大學出版社讀了即將出版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決定請志清來接替他的教職,為了堅持請志清,還自動拿半薪(見卷四,信件編號492,1961年2月17日,夏志清給濟安的信)。德威在哥大繼承了志清的位置,也繼承了志清的辦公室。德威多禮,讓志清繼續使用他肯特堂(Kent Hall)420的辦公室,自己則坐在對面蔣彝的位置──志清和蔣彝原共用一間辦公室,二人隔桌對坐。德威放假回臺省親,必來辭行,開學回來必先看我們,並帶來他母親的禮物。我們也視德威如家人。志清愛美食,吃遍曼哈頓有名的西餐館。我們去吃名館子,總不忘帶德威同去。德威去哈佛後,我們也日漸衰老,提不起去吃洋館子的興致了。 內文選摘(節錄) 夏濟安致夏志清(1965年1月23日) 志清弟: 來信已收到。我也好久沒寫信給你,很對不起。最近忙的還是所謂研究。《公社》那本東西居然得到倫敦大學的Kenneth Walker (經濟學家)來信讚美,說是fascinating & enlightening,這總算是空谷足音,很難得的鼓勵。我已寫回信去道謝,並問他可否為China Quarterly寫一書評。你很關心書評,如能得K.W.氏來評一下,那是比Fath Serruys或Goldman好了,因為他們研究的不是中共經濟,而我的著作是想enlighten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主流的。 這裡的language project的下一部作品,很快要動手。我本來擬的題目是《中蘇論戰中的rhetoric》,想向language靠攏得近一點。但是中蘇論戰最近幾個月較沉寂(但必將恢復,老毛是痛恨K氏路線,而K氏繼承人還是走K氏路線的),而我對於rhetoric的修養還不夠。我的長處是能夠吸收很多的information,而仍能整理出一個頭緒來。要發揮這方面的長處,還是研究中共的「社會史」。關於中共的農村,我的知識已經多得相當可觀,這一點也是可以利用的。現在決定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運動乍一看好像是老生常談,其實這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幌子。從臺北、香港來的報導,中共在城市進行「新五反」,在鄉村進行「新土改」,整治「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繼′60-′62之和緩政策後,猙獰面目重又暴露。但《人民日報》等中共報紙關於這方面的具體材料少極,祇說是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掩飾激發了我研究的興趣,我要用中共的材料,來說明該運動的真相為何。這樣非得大量的讀中共材料不可,即便以前讀過的,現在還得重讀,因為過去讀時,腦筋裡未存有這個題目也。這個工作,別人也無法幫忙,因為天下很少人有我這樣快讀的能力,吸收組織的本事,而且再有關於中共社會的基礎知識。興趣提起來了,所以精神很是煥發,《人民日報》之類的東西,假如不像我這樣有系統地讀,枯燥無比;一有系統地讀了,就成了學問,而且有發掘不盡的寶藏可得。 我這樣全神貫注的研究──我認為這是歷史的研究──當然影響我別方面的研究。以我的精神與努力,如研究中國社會史過去任何一個時期──從周朝到清末──必可成為專家,在學術界佔一席地,不讓楊聯陞、何炳棣(他可能來U.C.,接Bingham之位,B.要退休了)等專美於前。但是研究中共總是為學術界所輕視,這點我是很明白的。我的朋友Schurmann是「中共迷」,他說:「你能把公社弄出這樣一個頭緒來,如弄井田那是兩個禮拜就夠了」,以他的地位,當然可以為「中共研究」辯護。我祇是悄悄地做我的本份工作而已。但是心中也有點害怕:越深入,越和別的學問脫節了。我還有點關心:我到底在美國學術界製造了怎麼樣的一個image?
我越是努力,這里[裡]的language project恐怕將越是沒有人接得下去。吳魯芹當初有來加大的意思,但是我現在做的事情,他是接不上的。以世驤和Schurmann對我的友誼,我當然不忍看見這個language project垮臺。 我的興趣是研究,對出版等等倒是沒有什麼興趣的。有沒有書評,我更不關心。比起你來,我是很不career minded的。你寄來的那兩本蔣光慈,已收到,謝謝,但是還沒有開始看。我的文章,寫完就算,不想再去整理了,因為又有新的題目來把住我的注意力了。 Franz Michael決心辭職,改去華府的George Washington大學;最近沒接到他信,不知近況如何。想來他心境不很好,因為和多年老友George Taylor決裂,他心里[裡]不會痛快的。我的《左聯》一書,他是sponsor。現在U.W. Press要不要再出它,我也不知道,也懶得去問。一問之下,如是yes,那末我也沒有工夫來整理舊稿。這個事情到暑假時候再說吧。 心中慚愧的是:全書的introduction還沒有寫好。已數易其稿,但牽連東西太多,真照我的意思寫出來,恐不容易。 這是文債之一,文債之二,是欠Schaefer的那篇《西遊補》,初稿他看後大為滿意,但我不知道董說的《朝陽夢史》etc.,有沒有地方可以借得到,事情就擱下來了,其實發一個憤,一個禮拜就可以把《西遊補》趕出來,現在還是拖著。 周策縱那里[裡]還沒有寫回信,我想把〈蔣光慈〉寄給他,你看如何? 你的兩篇文章都收到了,都很精彩;當然為篇幅所限,有許多話你沒有地方發揮了。但是你的文筆還是遒勁而to the point的。Golden Casket的德文原本,Baner送我一本,但我一直沒有讀,雖然想improve我的德文,一直是我的志願。你所提起的中國小說中的love,也一直是我所想研究的題目之一。 我還沒有你這麼多閒差使(寫書評等),所以可以專心研究自己的題目。你擔任教書,指導論文研究,一定是很吃力的。我最近指導了一個女學生(去年在我班上的)研究周作人的M.A.論文,覺得此事很不易做。當然我對周作人的熟悉,不在世驤與Birch(他們也是導師)之下,但是周的全部著作我並未看過,有許多看過了也忘了,真要憑良心行事,我也得把周作人的全部著作看一遍。我相信我這樣指導,那位學生已很滿意了。但周作人是我比較熟悉的作家,真要指導起我所不熟悉(e.g.張資平)的作家來,那一定是很花工夫的。 我雖然覺得工作的壓力重,但是做人仍很瀟灑,不慌不忙,晚飯後不用腦筋,就是讀書也是讀比較輕鬆或與「研究」無關的,所以睡眠正常,精神很好。我發覺同事之間,不能睡覺的很多。世驤就依賴安眠藥,雖然他也打太極拳洗冷水浴等做健身活動。有個李卓皓,是個國際聞名的biochemist(研究hormone專家),他因為吃藥安眠加上吃藥提神,身體弄得衰弱不堪。另有一洋人,年輕時聰明非常,二十幾歲得M.D. & Ph.D.(生理學)兩個學位,現在不過三十幾歲,已成廢物,掛名做researcher。他的病源也是吃藥安眠,吃藥提神,二藥夾攻。他自己有行醫執照,可以亂開方子吃藥,所以危險更大。虧得他太太是個賢惠的中國人,服侍他。每晚十點鐘,一定要侍候他上床睡覺,看好他吃安眠藥。否則他糊里[�傒糊塗,不知道自己吃多少,可能惹出大亂子的。我的光華同學蕭俊亦失眠,以前喝酒安眠,後來想戒酒。到醫院驗身體,並請配方買安眠藥。醫生說:吃安眠藥睡覺,不如吃酒睡覺。這句話我很相信,因為人類與酒共存,已有數千年之久,酒的一切壞處,人都知道,出了毛病也查得出。安眠藥(尤其是新出的tranquillizer)歷史均短,到底它們有多少壞處,醫學上還沒有詳細記錄。怎麼出毛病,毛病出在哪裡,一時都無從查起。如安眠藥再加提神藥,那末奇奇怪怪的後果更多了。這些話說來給你參考,要請你「戒藥」那恐怕是很難的。照中國傳統思想,第一是樂天知命,第二是duty比health(or life)重要,所以我也不替你worry。不過美國的生活方式,一般都是緊張,靠吃藥睡覺與提神這個tendency恐怕越來越厲害。我生平沒有吃過提神藥,如No-doz之類我碰都不想碰,因為我精神一直不錯。安眠藥也是來美國以後才吃的,過去一年用了大約不過十次。用的祇是輕微的sleepeez,無需醫生開方子的,這種藥對於世驤已經是無效的了。我祇是在興奮和有心事時才服用,一年沒有幾次機會,平常是無需服藥的。 世驤於28日飛紐約,轉飛Bermuda,那天下午晚上他也許會來找你。Bermuda之會是為組織研究中國文學的工作立基礎,過去的進行,你大約有點知道。將來組織完成,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我對於這種事情並不十分起勁。研究中國文學就是這麼幾個人,大家都忙得很,也做不出什麼額外的工作。青年學者如Maeth等成名後,也無非軋在一起忙而已。將來可做之事,譬如編一部《中國文學史》,我就勸世驤不要答應擔承。因為請些誰來寫?誰來校訂?誰來替很多不同的投稿者劃一水平?小說部份可請你寫或請李田意寫,水準可能大不相同。做主編的忙死,還要得罪人,到時候可能交不出卷。世驤可能主持為《全唐詩》等巨帙做index工作,這種事情嘉惠學子,而且花了錢的確會有成績的,我很贊成。 我和R還是維持很好的友誼關係──就是這麼一點成績也不容易了。我顯不出什麼熱烈的愛,但做人到底比以前穩重機靈成熟多了。過年過節,男女朋友之間可能造成誤會,男的總想跟女的同度佳節,女的如忙,不能答應,男的可能比平常更為hurt。R不喜歡他的父母,但過年過節總要去孝順一番,這種事情我並不介意。說起來很容易,但你知道我並沒有頂頂sweet的脾氣,真能做到不介意也就是做到孔子的「恕」道了。最近出現另一個因素,虧得我心平氣和的對付得很好。即她過去的男友Charles Witke決定離婚,想和R.重拾舊好。按Ch.與R.過去的交情,我和她之間從來沒有做到這一地步;但在一年以前,R.把Ch.恨死,還是我去勸她饒恕他的。我知道此事後,心中不安(今年祇為此事,吃過這麼一次安眠藥),當時反應有二,一則決心退出,對R.表示冷淡,讓他們成全好事;或則加緊進攻,不讓「情敵」插足。總算我修養到家,二者皆未採取。對R.仍很誠懇忠實,既不洩氣,也不發狠。我這種態度,R.是很讚賞的。我的學問與wit,她本來很欣賞;還有一點是mature personality,我非得小心謹慎,不能保持也。Charles找我吃過一次午飯,長談很久,他和我之間無半點ill feeling(你得相信我的敏感,有半點ill feeling我就會覺出來的),這是我引以慰的。R.和Ch.已和解,但仍和我單獨出去。按加州離婚法,Ch.君要等一年才可離婚獲准,在此期間,他得小心做人,因為他的太太不願離婚,他如有失德之處,離婚可能不准的。R.自己的志向,還是去臺灣為第一要務──此事本來也可成為我和她之間的齟齬的因素的。我自己覺得是個很可愛的人,但戀愛經驗不足,在女人面前反而可能顯得不可愛。前年對B與Anna,都太慌張,這種缺點,我自己也了然。過而不能改,枉自為人。現在對於R我一直以可愛的姿態出現的,請你和Carol放心。以現狀觀之,R.決不願意丟掉我這麼一個朋友,好消息就是如此而已。 雖然我並不自覺陷入情網,看上面的描寫,你可知道我也不能全然無情。R.既occupy我的mind,所以也沒有工夫去對付別的女人了。 二月開始,我在comparative lit.的課又要開始。Compa. lit.方面可能以後還要叫我開一課seminar。但我目前忙於中共研究,這種遠景也不去多想。 你在紐約能夠看到中國電影,可以減輕你的思家之苦。對中國電影(香港拍的)我並無多大胃口。祇有一張凌波、樂蒂的《梁祝》可算上選(可能還是抄襲中共的東西)。此後看了李麗華、凌波的《新啼笑因緣》 與李麗華、嚴俊的《秦香蓮》 (包工鍘美案),看後直搖頭。Tempo都太慢,香港那些製片家對於電影的基本智識還得學習。 最近和R看了My Fair Lady與話劇Hedda Gabler 。前者我覺得很tuneful,值得再看一次。後者女主角Signe Hasso 滿身是勁,男主角Farley Granger 祇是英俊而已,演技平平,話劇的娛樂成份總很差,像Hedda Gabler那樣還算是好的。年前加州風雨成災,金山一帶亦陰雨連綿(大雨中世驤的車曾skid一次,車子碰壞,幸虧人無受傷者,我不在車內),幾個禮拜不停,學校方面平靜無事。Xmas假期過後,Savio再要召集大會,到場者據說僅二百人,二百人中不少還是「非學生」(馮雪峰等當年在北大亦是此種人也)。Savio的「群眾」本來就是這麼一些些,因為學校當局措置失當,才把事情鬧大的。 附上照片四張(「福祿壽」是在Schurmann家裡),並家信一封,希轉寄。別的再談,專此 敬頌
冬安
濟安
一月廿三日 Carol與Joyce前均此。 夏濟安致夏志清(1965年2月14日) 志清弟: 昨天接到來信,知日內正在搬家。今天買了木製果盤一件,平郵寄上,算是給你們的生日禮物並搬家禮物,日內想可收到。宋奇處久未通信,接奉來信很是高興。翻譯的事我想幫他忙,但commitments太多,不知時間是否來得及。他要2/15前有回信,但我回信尚未寫。如回信到得太晚,此事作罷,那麼我也無能為力了。 這幾天的心事當然是R,情形想必你在掛念中。此事現在看來必無好結果,祇看我是用什麼方式撤退耳。 對於R.,很奇怪的,我從來沒有真正fall in love。去年春天,她和Charles鬧翻,需要人安慰的時候,我當然待她很好,但是仍想法和她疏遠。去年暑假,我如真心想念她,中間可以抽一個時間回Berkeley來的;但是我舉止鎮靜,在暑假期間,她如找到別的男友,我可以很瀟灑地撤退。因此我在Seattle不慌不忙,坐觀其變。想不到其間毫無變化,她是真心等著我回來的。 暑假以後,我仍毫無表示。兩人date次數頻繁,一切對我成了routine。我除不表示「愛」以外,一切對她都很好。所以不表示「愛」的原故,第一,我心中並無此感情;第二,如一表示,可能造成緊張局面,破壞了我所享受的routine。 她在秋天決定要去臺灣,決定的時候,似乎很痛苦。因為過去B要去參加什麼Peace Corps,我去挽留也是白費的,所以我對R.不加挽留,雖然我心裡那時已若有所失。一表示挽留就是愛的表示了,此後我便將失去行動的自由。她對我的不加表示,似乎也失望。所謂「行動自由」倒並不是指「結婚」,而是她抓住我了,便可虐待我,我得仰她鼻息。 她雖然申請要去臺灣,當然她也知道去得成去不成與否尚成問題。我是盡力幫她忙的,但一切有賴於她的是否能通過「博士」預試;即便她什麼成績都很好,但名額有限,別人已經等了好幾年的,可能有優先權先去。既然誰都沒有把握她是否能去得成,我也犯不著著急。 此後一直很順利,直到Charles的重現。她是十分喜歡Charles的。她的來Berkeley是C.幫的忙,因為C.在這裡找到事情了,甚至她和她前夫離婚,我猜想C.在其間也有作用。C.並非壞人,讀的是古典文學,為人迂腐,而且拘謹,天才絕不橫溢,守著自己的範圍與career,有點寒酸的樣子。 她和C.在開頭好的時候,我當然絕不曾想到會插足進去。她和C.鬧翻了,把他罵得一文不值。我還勸她不要如此趨於極端,我說C.的痛苦不在她之下,她應該原諒他。同時一個女人如此痛恨一個男人,我也覺得她愛他愛得很厲害。 他們鬧翻的原因是C.的太太忽然殺到Berkeley來。該婦我見過一次,既老且醜,據說甚為潑辣。她到學校系當局去告C.的狀,並到R.的寓所去大鬧。C.君束手無策,護花乏術。R.那時把她[他]恨死了,這大約是整整一年前的事吧。她恨他沒有男人骨氣,不敢和他太太離婚。 此後她和C.在學校里[裡]偶然見面,見面情形她總是告訴我的。他先是不理她,她更恨。後來漸漸講話了,但至少在暑假裡還是沒有什麼動靜的。暑假以後(月份忘記了),她告訴我一件事,當時我沒有在意,因為她祇是重申C.的不中用而已。那時C.忽然決定與太太離異,搬到外面去住了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之後,不耐寂寞,又搬回太太那里[裡]去了。R.描寫此事時,對他嗤之以鼻。其實當時情形已經不妙,至少C.的生活情形,R.還是知道的。C.的決定搬出去,也許是受R.的影響,但C君再度表現懦弱,他和R.感情一時又無法恢復。 Thanksgiving R.回到Los Altos她家裡,同時去Stanford利用假期翻查參考材料。回來告訴我又和C.君見面了。C.君恰巧那時在Stanford開會。他們談話情形我不知,但是據事後發展觀之,他之決定離婚大約就是和R.在Stanford談話的結果。 R.的開始對我表示冷淡是在′65年的一月,當時她又要忙著回家,又要忙著準備考試,她又popular,有各種parties要參加,我並不在意。一月十日我發見[現]他們兩人在一起,知道情形有大變化。因為別的追求她的男子,其地位皆遠不如我,我根本不放在心上。C君的出現,對我才是極大的威脅。次日,C君約我吃午飯,告訴我他已決定和太太離婚。 我後來見到R.多次,我當然仍裝作瀟灑狀。我說要退出,她不許。她說We shall all become friends。我說You prefer Charles to me,她說沒有這回的事。我說You are committed to Charles,她說In a way I am committed to you too。我說以後週末不來麻煩你了,她說Don’t be silly!她說她最希望的不是結婚,而是去臺灣留學。話雖如此說,但態度總有點不大對。 假如我現在有事情要去Seattle幾個月,就此把她丟了,我毫不感覺痛苦。但在學校裡大家常見面,而局面尷尬,使我很為難。我的根本態度是絕不和C君去爭,對於R.則想在好下台的狀況下下台。我的考慮老實說不是愛情,而是「面子」。 最近幾天,事情頗有反覆。假如男女雙方是鬥智的話,那麼我失敗得相當的慘。 週末我本來已是不去麻煩她了。星期一(二月八日)晚上學校有演講,講完後我開車送她回家。我訴了些苦,她對我很好。她說我們之間的誤會是由於我對Charles的hostility,我說沒有的事。她說:「本來嚜,我相信你larger than that。」這點誤會講穿,一切都很好了。我約她星期三吃晚飯。 星期三(二月十日)我們在金山Omar Khayyam吃晚飯,恢復過去的愉快。誤會消失很多,她說她過去幾個星期對我neglectful,她現在plead guilty(那天大談我們要合作編一部Anthology of Communist Chinese Literature,她非常高興,預備暑假開始)。最後送她回家,她非常高興地說:You are capable of making people very happy。 情形雖然好轉,當然你可想像我可不是會輕易得意忘形的人。我仍舊預備撤退,但兩人在愉快狀態中漸漸疏遠,這對我將是最好的辦法。 星期五(十二日)晚八點半,她在寓所預備了Venetian Coffee、Coffee Cake、Chocolate Roll舉行Party,客人約十二名,別的都是已婚的,有逐鹿資格的祇有C君與我。她既然說我有hostility,我表現得很大方,相當幽默。經過星期三的事,我心情頗好。我既不存心追求,她能待我如此,我已滿足。我決不和C君去奪美的。
星期六(十三日)忽然局勢大變。原定計劃是我決不去佔有她的週末,也決不去佔有她的Valentine’s Day。但V.D.既近在目前,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尤其是經過星期三的愉快的談話,我應該表示得熱烈一點。 本來就慶祝V.D.而言,我對於R.可有三個方式,我都考慮過的:一是無所表示(假如她繼續冷淡的話);二是輕淡表示,三是熱烈表示。在目前狀況之下,我的熱烈當然很有限度,但她既口口聲聲說我們是朋友,我就在「朋友」上做文章。 星期五的Party,我帶去一本厚書:A History of Japan in Art,她一直喜歡這本書,從它出版時候開始。我本來可以在聖誕節送她,但聖誕節送她趙元任一套唱片,比它更貴重。這本書我預備留著到她生日時(三月)或其他機會時再送。 同時我精心做了一篇小文章寫在卡片上一併送去。文章是這樣的: Dear R:
Owing to your sweet & compassionate nature, you perhaps will never exclude me from your blessings on this or any other day. The largesse of your heart, indeed, is the basis of our friendship which I do cherish. But the friendship I am celebrating, in the revivifying air of the early spring, is a friendship whose beauty & strength comes from an intimate &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 sharing of confidences & a reciprocation of affection, a mutual inspiration & elevation; it comes from even an idealism in which I believe we share our faith. It is a friendship which adversity may test but which nothing except selfishness can impair, which sensitively responds to cultivation though the blissful enjoyment of it is also a form of cultivation, which enriches life & is enriched by life, & which imparts sweetness & light to the world.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saint who provides occasion for the expression of this friendship though, as you well know, as beautiful thing in the world needs expression: it grows in the feeling. As ever,
Yours devotedly,
Tsi An (你覺得這些話是否過火?望告) 這種話我們平常談話中也說,當然寫下來後,比較漂亮。我把禮物帶去,她打開一看,十分高興。我說「卡片上的話我認為比較更重要,你以為如何?」她微笑說:「I Like it very much,可是晚上我還得仔細看看。」我因為我的英文相當深,她又要招待客人,又忙於翻看那本書,她一下子沒有得到深刻印象,所以我對她的反應沒有放在心上。在party裡,她是個出色的hostess。對任何人都很好,對我也很體貼。我mood很好,臨走時大家很愉快,我說:I shall call you,她說fine。
星期六的電話使我手足無措。電話裡我先問她碗洗了沒有(她臨睡前就洗的),晚上什麼時候睡的,早上什麼時候起來的等等廢話。她忽然說:「你的禮物很splendid,但是太重了,而且你卡片裡的spirit也不是我所能接受的,所以我想把那書送還給你。」這個晴天霹靂我毫無防備,一切瀟灑歸於泡影。我很生氣,我說:「我看不出卡片上的話有什麼不對,你不喜歡,燒了它好了,書務請留下。退書給我的打擊太重,你想我應該受這個打擊嗎?即便我的話得罪了你,你的反擊也太重了一點,書你先收下,以後的事,一切由你決定,我希望我們是還能維持舊歡的。」她說:「I hope so.」聽她口氣,以後對我又要恢復冷淡了。 假如我真陷入了情網,這個打擊將是十分慘重;即使像現在這樣,失敗也相當的慘。禮物她是喜歡的(她還拿給朋友們看),卡片上的話假如早些時候寫了寄去,她也許會喜出望外,或者也許會尊重禮貌地表示感激,現在居然表示拒絕接受。虧得我說的不是愛,祇是友誼,而且態度大方,無半點肉麻,她要拒絕,實在也說不出理由。 像現在這樣所謂「友誼」云云,實很難維持。友誼之斷絕在我大做「友誼論」之後,也是天下一大諷刺。表面上還不至做到雙方見面不理的程度,但是朋友貴在雙方相知,她若事事挑剔,我將不勝其繁。她第一挑剔是我對Charles的hostility,其實這是毫無根據的(根本有一段時間我沒有見她的面,也沒有見到他的面,她怎麼知道我有hostility?);現在又來挑剔我的文章態度不對──照我過去所了解的她,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朋友見面,老是質問或解釋,這種朋友也沒有意思了,是不是?)。 我祇是臉皮嫩,怕朋友間笑談(尤其是Grace),否則的話,要斷絕是很容易的。和R的下場如此,真是意想不到的。當然,和她這一段友情,也是意想不到的。你總還記得,在一年之前我口口聲聲說要過一個「無女友的生活」了罷。R的出現,並對我事事遷就表示體貼,我當然是感激的。現在緣份已盡,到此為止了。 此事要是給我什麼教訓,那就是:男女來往(不管是否談戀愛)還是誰征服誰的鬥爭。我和R之間,直到最近我是不屈服的,即表示不在乎,不追求,隨她去。她表面上雖處之泰然,心中(也許是下意識的)一定不服氣。C君之重現,我有極短時間還認為她來試我的心的──當然現在是很明顯的表明她心目中是祇有C君的了。但她利用C君出現的新形勢來逼我(可能也是下意識的)有所表示,因此她忽鬆忽緊,開始把我玩弄於股掌之上,等到我一有表示,她立刻在戰略上取得絕對優勢,以後天氣陰晴寒暖全聽她的了。如此關係一緊張,必無好下場。我跟Anna的關係也是如此:經過的階段是(一)她對我大表好感,(二)我那次是為感激,也表示愛情;(三)我冷淡;(四)緊張破裂。 對付緊張狀態一定有一套藝術,大約是同打Poker那樣的「狠,穩,忍,準」四字訣吧。這套藝術我從未學會,而且人生責任太多,無暇去深究;play the game花的精神太多,非我所能應付。還有我的性格裡還是有太多的嚴肅,真是遊戲人間,倒是可以無往而不利的。假如R說:「書我想退還給你」,我哈哈一笑說:「好極了,我現在就來拿吧」,這一下會把她搞得手腳無措了。但是我雖足智多謀,深謀遠慮,能料能斷,但是真逢到事情還是手忙腳亂的。話說得越多,越顯得笨拙;自己越恨自己,就越發的不瀟灑了。(14日附記:她如真把書退給我,我現在預備收下來了──一切順著她!) 事情如此下場當然使你失望,我很抱歉。你來金山開會,我可能還會把她介紹給你,那時你可以想像:我們之間貌既不甚合,神亦大離的了。但是她很會做人,對人一般而言是很和善親熱的,你可能仍舊會喜歡她。 此事主要關鍵,還是「她不愛我」。為什麼她不愛我,我的解釋是因緣問題。你也許會說:我對她不表示愛,她怎麼來愛我?情形並非完全如此。第一,很多美國青年追她,都以熱烈求愛姿態出現,她都不喜歡,她說她喜歡我就是喜歡我的做人作風。第二,我在卡片上寫的sharing of confidences & a reciprocation of affection不是瞎說的,我們之間的交情是達到這個地步。我在西雅圖寫信告訴她說害了重傷風,她特地打長途電話來慰問。但交情祇到此為止,假如她心底下真藏有一份更深的感情,C君根本插不進來;而且我一著急,她應該立刻來安慰我才對。那時的著急雖不算大痛苦,但我是等著她來安慰的。重傷風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念她。 此後可能又是無女友的生活了。當然你會想起B,我們之間還是很好,但是我對她感情日淡。要date她還是可以的──當然以後要date R還是可以的,就看我肯不肯而已。但近乎敷衍的date是沒有什麼意思的。V.D.日,我叫花店送一盆Azalea給B,卡片上祇寫with best wishes from T.A.,她收到後祇會感激,決不會來說什麼退不退的。 還有一個中國小姐叫Amy(廣東人講上海話),讀zoology,現在已在某小大學(Hayward)兼課教書。這位小姐我開始認識她還在1960年,彼此印象都很好。從那時開始,不知多少位青年去追求,敗下陣來,我是冷眼旁觀。最近有機會碰見,我獻了一番慇懃。她明白地表示很願意和我一起出去。我最近有點像驚弓之鳥,對於這位拒絕了很多青年的Amy小姐,更得小心翼翼地對付。我現在按兵不動,顯得我作風的穩健──我說「彼此印象很好」,我祇是憑穩健給她好印象而已。但你一定很高興的知道,在R動搖的時候,我在別的地方也放下埋伏了。 我現在的心事並不是失戀的痛苦,也不是埋怨老天爺的作弄,祇是覺得有點尷尬(而且我一點也不恨C君,這點恐怕使他很難相信)。祇要男人不陷入情網,女人是拿你沒有辦法的。我相信我沒有真正愛過R,這是我的不是,但是在目前狀況,這又成了我的「資產」了。我還可以穩紮穩打,求一個面面俱到的解決辦法。對於最近那一段慌張,也並不怪自己──任何人碰到這情形,也很難有更好的對付之道。我總算是個有經驗而且能沉得住氣的人了。 世驤從Bermuda回來,會議情形對我說了。1967年之會我應邀出席,算是大幸。虧得我的《下放》、《公社》那些作品沒有人寫過書評。假如人人皆知我寫過那些東西,恐怕我的出席資格一定要不被通過的。Hightower反對你,你也許從劉若愚那里[裡]聽到了,希望你不要生氣。你祇是算把你的出席資格讓給你的哥哥了吧。 寫到這裡,關於R還有一事可說。即C君的離婚官司在加州打起來將大費周折,蓋C君之妻未必「伏雌」也。此事我可不關心,祇是希望他們之事順利解決,如R牽連在內,她必大感痛苦。R愛C君,我又不愛R,其間本無三角關係在內。我之慊慊於心者,是如何與R維持「友誼」關係也。「友誼」而如此吃力,那可就難以維持了(她三月過生日,我仍會送禮物去)。 我工作如舊,精神也很好,請你不要掛念。新居想必使你們身心愉快。別的再談 專頌
近安
濟安
二月十三日
Carol與Joyce前均此。 P.S.十四日晨又及 寫上面這封信時,顯得很生氣,昨晚一覺睡得很好(當然不吃藥),今晨已心平氣和,可以把問題再概括一下。我和R之間交情非淺,而且學問上公務上尚有往來,所以除非雙方有一方決心斷絕,斷絕是很難的。我自以為是個tactful的人,平日少有忤人之事,當然盡可能的不去得罪她。我喜歡R這個人,但是討厭R這個問題。為了要丟開這個問題,寧可丟開這個人。其實對付問題的方法還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或者老子的「無為」,即:我得少緊張,當它沒有這回事。咬牙切齒的決心這樣決心那樣,都是不對的。我的脾氣還得更為圓通。 說起Amy,或者引起你很大的興趣。1960年Grace舉辦Fashion Show,中國小姐十二(?)名參加。小姐中姿首不一,但談話頂有風趣韻味的,是她。1960年那時,我見什麼小姐都不動心的,而且追一個popular的中國小姐,徒惹大家閒話,引為笑柄而已。事情就一拖四、五年,我們不常見面,見面時談得也不多,但雙方總留點印象吧。′64年底前碰到,她還complain,說我從來沒有去請過她。看樣子她並沒有熱絡的男友──這許多suitors被打退,別人想都寒了心了。她雖然有這麼明顯的表示,我還是按兵不動。這回我非得十分審慎不可。別人(包括有我所認識的)之敗,都是敗在太猴急上。我能等四五年,難道不能再等幾個星期嗎?同時,我可以跟她通電話,拜訪她,先把情形摸清楚了再動。她是歡迎我去date她,但是date的方式與勤度,我還得好好考慮。第一原則:不能露出半絲半毫的「愛」意,露了半點,情形就難辦了。女子大致都是如此,Amy有record在,情形更是如此。你可不要說:小姐越擱越老,難道她們不著急嗎?(′60年時,Amy剛從Bryn Mawr畢業來加大,風頭很健。)這種話對小姐缺乏尊敬,白克萊著急的小姐多的是,她們豈在我眼裡?Amy如著急,當不自今年始。她過去不肯遷就,現在也未必遷就的。她是個頭腦冷靜之人,而且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我可以把問題跟她談白了再開始行動。去年Xmas我送了她一本你的《小說史》。 對於B,我是上來先慌,現在居然還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原因我猜是為了R。祇要R跟我不斷,B一定對我好;B若知道我們間有了變化,她立刻會戒備,我去找她也許沒有這麼容易了。 對於Anna,開頭自以為很穩當,不久即步驟大亂而垮。對於R,我穩當了很久很久,雙方的確維持一個十分愉快的關係。想不到現在步子又亂了。步子已亂,當得冷靜一個時候再說。我真想出門一下,不見她一、兩個月,回來後一定可以恢復很好的關係(當然不如以前了),我心中惱恨的是無法走開,而且常常見面。我的尷尬樣子老在她面前轉,我熱也不是,冷也不是──這就是我所謂「問題」。 當然你還想起S。此人我並不討厭(as a whole),雖然性格上有許多地方太需要修改了,但我絕不會惹她。她現在拜了Grace為乾媽,而Grace一心希望我和R之事垮掉。有許多型的小姐是不能找的,其中之一是「有封建關係的不能找」。惹了S,等於使得我和世驤、Grace的關係增加複雜性。我露出半點對S的興趣,或者露出半點我正在寂寞需人安慰的情形,Grace就來動員了──這個,老天爺,我是受不了的! 今天是V.D.,按理說我可有個date,但是我還是預備安心工作,晚上也許一人去看個電影。R是定給C君了。B和Amy都可以找,但一找B,她立刻會警覺我和R之間出了事;Amy那裡,關係尚未開始,定這麼一個日子來開始,祇是刺激她的警覺性而已(Amy知道我有R)。而且我得假定B和A這一天都有男友約會的──假如被我發現她們沒有男友約會,她們將很失面子。正如我如被她們發現沒有女友約會,我將認為很失面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之謂也。 想不到這麼大年紀還在風月場中顛倒,一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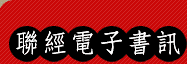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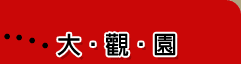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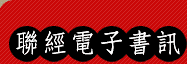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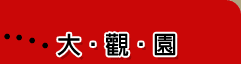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