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禮讚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新中國建立。
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遷移台灣,新台灣從此誕生。
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1949,1949年之於新中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
1949年之於新台彎,則是文化的意義。 序一(節錄)
納中華入台灣/王德威 楊儒賓教授是台灣思想與文化史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對新儒學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視。在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他推出《1949禮讚》,作為回顧台灣歷史、縱觀中華文化的反省。這是一本奇書,選在此刻島上如此躁鬱不安的時機出版,尤其意味深長。 一九四九是個危機四伏的年分。這一年共產黨席捲大陸,成立人民共和國。國民黨退守台灣,延續了民國命脈。兩岸自此對峙,時至今日,仍然無解。一九四九也是充滿創傷的年分。六十萬國軍殘兵敗將退守台灣,近百萬大陸難民倉皇奔逃海外。而島上人民在二二八的劇烈考驗後,短短時間又被拋入另一波戒嚴戡亂的狂潮中。恰與人民共和國的論述相反,一九四九帶給我們的聯想是失敗、離散、恥辱與憂患。 楊儒賓教授理解這些關於一九四九的記憶,卻另闢蹊徑,提出不同看法。他要為一九四九貫注正能量。他認為,一九四九年所帶來的遷徙與暴虐固然血跡斑斑,但從大歷史角度看,台灣因緣際會,卻成為華族文化最近一次「南渡」的終點。永嘉、靖康、南明,無不是分崩離析的時代,但北方氏族庶民大舉南遷,帶來族群交匯,文化重整,終使得南方文明精采紛呈,以致凌駕北方。 台灣在非常時期,承擔了不可能的任務:不但接納了北方的軍民,也吸收了各種知識、文化資源。自由主義的民主思考,儒家的禮樂憧憬,還有殖民地時期的摩登文化在此相互激盪。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有識之士不分本土外來,持續他們的理念與堅持,多少年後,才有了今天眾聲喧譁的局面。楊儒賓因此反問,如果沒有了一九四九,沒有了台灣,今天以共產黨統領的「中國」文化,還剩下了什麼? 台灣政治在太陽花運動後有了大翻轉。在反中成為時尚的此刻,本土的愛台的楊儒賓無疑干冒大不韙,寫出統獨兩面都不討好的文字。他至少觸犯了三項禁忌。他「禮讚」一九四九,推崇台灣作為「南渡」文化的終點,儼然將台灣置於大中國歷史的脈絡裡。這令死守台灣「主體性」的忠臣義士們情何以堪?其次,楊儒賓認為中華民國政權縱有千般不是,但為台灣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觀念、主權意識、文化傳承帶來基礎,即使以反面教材視之,依然有其貢獻。這樣的論點中共政權必然側目以對,獨派人士更要興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怒。同樣引起爭議的是,楊儒賓強調儒家所蘊涵的人文願景及「東亞民主」模式,因為一九四九以後的台灣,有了綻放的可能。對此奉行種種時新主義的同僚要斥為保守,而在「孔子學院」氾濫全球的今天,他的立場也似乎左支右絀。 但細讀《1949禮讚》,讀者會發覺楊儒賓的論述遠較上述複雜。我們可以挑戰他的論點,但無從忽視他的用心。越俎代庖,我對上述論點有如下三點理解以及辯難。 楊儒賓談一九四九與「南渡」,批判者可以視為對他大中國文化的效忠,殊不知這些批判者自己才是最效忠「中國」的一群人。他們眼中只看到一以貫之的中國,並且無限放大,因此也無從擺脫愛恨交加的情結。楊儒賓提供的視野,與其說強調「中國」傳統的賡續性,不如說是提醒「中國」傳統的斷裂性。作為國家政治實體,「中國」是現代的發明,歷史不過一百多年;作為一種文明衍生的過程,「中國」的駁雜與裂變千百年來未曾停止。 我認為「南渡」作為事件,本身已經帶來歷史、文化、政治的質變。如果「南渡」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就隱含了中華文化內部衍異、斷裂,寄生,再生,甚或滅絕的可能。楊教授批評者,不論紅藍綠,困於古典的一統史觀,不願也不能耐心看待這一論述的顛覆意義。許倬雲、葛兆光等學者近年一再提出華夏文明內,華與夷、漢與胡的此消彼長,自古已然。五胡亂華、永嘉之亂後,中國北方有四百年由胡人統治,華夷混雜自不待言,而南下漢人對南方種族文明的吸收或融入,不斷產生奇花異果。靖康之難以後,南北人口大遷徙,南方氣象一新,北方燕雲十六州等地則有八百年不屬華夏「正朔」。更不提蒙元和滿清「外來政權」對整個大陸的統治。 當彼岸大一統論述鋪天蓋地而來時,楊儒賓思考大一統的對立面。這一對立面裡有多少朝代、「國家」、種族和文化興衰起滅,懶人包版統獨論哪裡願意正視?在一九四九這樣的時間點,歷史陷落,政權遞嬗,楊儒賓看到中華文明──或他所謂漢華文明──又一次轉型。血腥苦難的代價已經付出,後之來者除了銘記、檢討創傷與不義,也更要化危機為契機。這是楊的願景,也是他解釋,與解構,大中國史觀的方法。 與此同時,楊教授一片菩薩心腸,遮蔽了「南渡」的陰暗面:歷史上南朝的命運多半不堪。遠的不說,一六四五年,當清軍已經兵臨南京城下,南明弘光帝小朝廷還在酣暢淋漓的黨爭內鬥。鄭成功獨力開台不過三代,就被自己的子孫送交「清領」。歷史的詭譎恰在這裡,知識分子的願景和政治現實之間的齟齬從來如此。 這就帶到楊儒賓面對中華民國與一九四九的態度。中華民國是現代「中國」的肇始者。如識者所論,這一政權一方面推翻封建皇權,卻也繼承其領土主權與政治合法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延續這一矛盾。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迫遷台灣,風雨飄搖中對政權的保衛不遺餘力。七十年代後,共和國進入國際舞台,民國的正統性愈益受到挑戰,何況島上自決意識的興起。過去二十年來歷經統獨攻防,「台灣」必也正名乎的口號甚囂塵上,「中華民國」已經被幽靈化。 序二(節錄) 黃土地與藍海洋/陳怡蓁 楊儒賓是我的大學同學,我們這一班至今仍然時相往還,親愛精誠。同學們嬉笑怒罵,挖苦打鬧,從不避嫌。然而對外人,我們都羞於承認是儒賓的同班同學,不是為怕他滿頭白髮洩露了共同的年齡機密,而是唯恐別人誤以為我們的學問都跟他一樣好。 儒賓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中文系,早有青雲之志,數十年教書研究從不改其樂。從楚辭、老莊、易經,到瑞士心理學家卡爾.容格,他研究的範圍何其深廣,旁徵博引,總能以獨到的創見啟迪人心。我雖然老愛打趣他、捉弄他、跟他抬槓,其實偷偷認真拜讀他的論文,當真是「我腹無才,得三分之教,茅塞頓開」。 近日他忽然傳來一疊論文,說即將出書,囑我作序。這次的議題更具爭議性,竟是才不過一甲子之前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 我雖常為人作序,卻多是吳儂軟語,隨興而作。為「一九四九論」這樣擲地有聲的論述作序,深知自不量力。但是捨不得放棄沾光的機會,再說既然另有重量級學者王德威作序,我的序自然不足為觀,也就不必羞慚,因此大膽承應,同時決定保持軟語本色,也好讓人知道同學不一定同才。 說到一九四九,通常我們想到的是「撤退」、「遷台」、「毋忘在莒」這樣帶著創傷的字眼,儒賓卻別出心裁、隆重地用了「禮讚」。 他聚焦一九四九年,卻如鯤魚化大鵬,翱翔於歷史的縱長與雲空的廣袤之間,將我們帶向不一樣的視角,看見不一樣的一九四九。 先看那片黃土地。千年的歷史是千年的流徙,自從永嘉、靖康、南明以來,漢民族早就不斷南遷,台灣或許可以說是遷徙的最後一站。 再看這片藍海洋、海洋上最美麗的福爾摩沙島。四百年的歷史是四百年的海納百川。不斷接納著四海而來的移民,最關鍵的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驅荷入駐,一八九五年日人據台,然後就是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退入台。 黃土地與藍海島嶼的接榫原來竟是既定的走向,也是必然的命運。 對島嶼來說,每一次的移民潮,都可視為一種入侵,帶著不可避免的威嚇,甚至改朝換代的傷痛。一九四九從政治面來看苦難從未間斷,高壓統治、二二八、白色恐怖,誰言容易忘懷?但是如果抽離政治,換個角度從文化面來看,島嶼的收穫卻是無與倫比的璀璨輝煌:大批的文官、學者、作家、藝術家、教育家,帶著深厚的文化根柢以及敗戰後的省思而來。為了維持法統而建立的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等等,意外地使台灣從偏安一嶼的閩南文化、殖民文化,躍升而為中華文化的主流,進而擴張影響到南亞,立足世界而無愧。 此所以儒賓要「禮讚一九四九」! 作為同學的我,卻不免要擔心,出身中台灣農家,任教於清華大學,又曾投身反對運動,儒賓的「禮讚」難道不怕背負「賣台」的恥笑嗎?所幸書中蘊藏在禮讚背後的,是一片顯見的苦心孤詣,他細述災難帶來的歷史機會,更肯定台灣本土的創造力。一介書生耿耿直言,但求有益民主社會,無愧歷史長流,雖千萬人吾往矣! 移民固然帶來豐厚的文化資產,然而如果不是台灣人民本性的堅忍寬厚;如果不是暗自茁壯在日本侵略之下的台灣漢文化;如果不是長期的接納所養成的胸襟與胃口,怎麼可能承載得起這樣突然而至的大量、重量又多省多樣的移民?怎麼可能消化得下這樣滿漢全席的文化饗宴? 自序(節錄) 這本書本來是為作者個人而寫的,沒有成書的預期,它只是個人尋找自我定位的紀錄。身處八方風雨交會的島嶼,不管是個人的或是社會整體的方向,都不是那麼容易摸索出來的。我先是心虛地反思詰責,獨白式地自我與自我對話;接著或正經或不正經地將個人的反思化為群議的話題,有人贊成,自然也有人反對;然後因緣聚會,遂有文字。 有了短文,對自己已有交代。這些短文如果能靜躺於期刊或電腦中,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本無不可。書內的文字多是常識之言,常識到日常空氣的程度,沒有什麼好張皇的。但我們這個島嶼有些特別,常識通常特別缺乏。有些朋友看了書中的一兩篇短文,頗有感,認為我的常識不見得那麼「常」,「識」至少是見仁見智,但島嶼上應當有此一論,借以中和空氣中一種過度炙熱的有識之見。 作者生在冷戰形成不久的年代,距離一九四九大撤退不過七年,我們這個年代成長的人是呼吸冷戰時期「不沉的航空母艦」上的空氣以建構主體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是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台灣的想像,也是台灣當局時常用以自我安慰的咒語。在一次聊天中,一位政大哲學系的朋友說道:「我們這一代的人的生命是有共性的,大家閱讀廣文書局的一些新儒家文字、商務印書館的一些錢穆著作、慧日講堂的一些印順佛學、志文出版社的西方翻譯、水牛出版社的存在主義文本。接著是進入大學後的戒嚴法鬆懈時期,我們從黨外雜誌獲得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我們從台大、師大附近的書攤,獲得課堂上學不到的另一批左派的知識。於是平靜的知識基盤開始搖動,接著世界觀動搖,然後是懷著各種不徹底而聊可自贖的心情進行反叛。」 這位朋友說得很實在,我與周遭不少朋友都依循這樣的軌道長出了自我。我們這群在後一九四九大分裂時代生長的人別無選擇地,被命運狠甩在東西衝突與古今交會的銜接點上。我們個人生命的成長與框住我們生命的世界一起演變,時代的浪潮推著我們穿越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以至即將被穿越的馬英九的時代。然後少年子弟江湖老,憤青被流光帶入哀樂交集的中老年。 我們成長的共性是我們行動的原點,它框住了我們的視野,框住既表示具體化,也表示限制。不知從何時起,或許從國會全面改選後,我覺得自己已不需要耗神在偉大的政治議題,人生大有事在。但反而在政治熱退燒後,竟開始懷疑自己到底對台灣了解多少?懸疑逼出通路,我的撤退反而導向了另一種方式的進入,我逐漸相信內藤湖南的「文明遷移說」有相當的解釋力道,台灣可能是漢文化南移在地理上的終點站,而一九四九則是漢人南遷在歷史上最後的一波。很湊巧地,我的結論在姚嘉文律師於獄中撰寫的《台灣七色記》裡找到了印證──雖然姚律師可能不贊成這本書的論點。 本書原來以「1994論」命名。劉勰說:文體的「論」字意指「述經敘理」,高頭講章,莊嚴得很。本書如何能論?思考再三,乃易今名。筆者當初所以想加「論」字,只是表示此書確實代表一種史觀,一種與個人存在的價值觀息息相扣的視野。書中論:一九四九是中國史上第三波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大移民潮;是台灣史上最關鍵的年分;民國學術是台灣學術的骨幹;台灣的存在對整體華人文化有獨特的意義,若此總總,信者自信,疑者自疑,歷史解釋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沒什麼不可以論的,也很難說服別人自己的拙見到底有何卓見。但竊以為台灣輿論輿圖上若少掉此段議論,總是遺憾。 內文選摘(節錄)
1949的禮讚 一九四九年,一個不太受世人注目的歷史年分,此年歐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除了這個事件較受注目外,美、亞、非洲個別地區都有些騷動,但都不成氣候,相對而言,世界局勢可謂大體平靜無波。此年上距一次大戰善後會議的巴黎和會,恰好三十年,距離引發中日十四年戰爭的滿洲事變十八年,離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已四年;此年下距古巴危機十三年,離越戰結束二十七年,離象徵冷戰體制崩潰的柏林圍牆倒塌四十年。比起上述的年分,一九四九此年在歐美史上或第三世界史上,都沒有太重要的地位,它似乎是個可以被忽略的數字。但一九四九此年在兩岸關係上卻是舉足輕重的,此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國,新中國建立,爾後的世界政治版圖就此全面改寫。此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遷移台灣,在一種更深層也更悠遠的意義上,新台灣從此誕生。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之於新中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一九四九年之於新台灣,則是文化的意義。 一九四九年是台灣的年分,它賦予台灣一種歷史定位的架構,台灣則充實了一九四九年在東方歷史上的意義。縱觀台灣四百年史,歷史斷層特多,文化意義的累積常無法連貫。大斷層的斷裂點通常是政權的遞換所致,而隨著政權的遞換往往會帶來移民潮的湧入。就漢人的觀點看,一六六一、一八九五與一九四九當是台灣史上三個最關鍵性的年分。一六六一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歐洲海權在台灣的擴充行動戛然中止,漢人移民作為台灣社會變遷的歷史主軸就此奠定。一八九五年日人據台,台灣很快的淪為新興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這個島嶼迅速的捲進了「文明化」的現代性行程,它領先它的大陸兄弟,進入現代的世界體系。一九四九年的歷史地標則是國民政府敗退入台,撤退雖是內戰所致,但也是尖銳的意識型態鬥爭的結局,其結果則是前所未見的大量移民湧入台灣。在這三個轉折期中,一九四九年的移民潮數量最大,改變的社會結構最深,牽動的國際因素最複雜,但也最有機會搭上歷史的列車,讓台灣走出灰白黯淡的默片時代。 在三波的大移民潮中,一九四九年所以特別重要,乃因當時的移民集團是以整體中國格局的縮影之方式移來台灣。我們不會忘記,也老是被反對運動人物提醒:一九四九是個受詛咒的歲月,因為純樸的島嶼此年被一個由失意政客、殘兵敗將所組成的政權污辱了。這個失德的政權被趕出了中國,它轉進了台灣,隨後卻將這塊救命的島嶼塗抹成所謂的自由中國。這種比例失衡的中國架構加上舊中國的官僚作風,曾帶給台灣相當的痛苦,讓它在政治的轉型運作中充滿了難言的斑斑血淚,也使它在爾後的國際活動空間中,嘗盡了苦果。一九四九的痛苦是歷史的存在,解釋不掉的。不管對新移民或舊住民而言,他們都被迫要面對一個陌生的處境,他們一樣有不堪的歷史記憶──只是不堪的面向不一樣。一九四九的台灣被籠罩在一片完全看不到陽光的陰影中。 但台灣背負的中國格局不盡是包袱,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面向也不容忽視,正是因為敗退的國民政府抱著代表中國正統的想法,所以才會有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這種世界級的文物進駐台灣,也才會有代表中國頂級學術文化意義的中央研究院、國史館、歷史博物館等機構文物進入此一島嶼,其他各級殘缺不全的政府組織也因應時局輾轉入台。物華天寶,千載一會。不誇張的說,一九四九年湧進台灣的文物之質與量,超過以往三四百年的任一時期。文物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因素,除了眾所周知的大量的軍警人員外,最頂級的大知識分子與為數不少的中間知識分子也因義不帝秦或個人的抉擇來到此地。他們參與台灣,融入台灣,他們的精神活動成為塑造今日台灣面貌的強而有力因素。 台灣無從選擇地接納了一九四九,接納了大陸的因素,雨露霜雹,正負皆收。結果短空長多,歷史詭譎地激發了台灣產生質的飛躍。但獨坐大雄峰,誰聽過單掌的聲響?中國大陸的文化與人員因素也因進入台灣,才找到最恰當的生機之土壤。在戰後的華人地區,台灣可能累積了最可觀的再生的力量,其基礎教育、戶政系統、公務體系的完整都是中國各地少見的。台灣人民的祖國熱情雖然在前兩年的浩劫中被澆熄了一大半,但「艱難兄弟自相親」的情分猶存。更重要的,台灣在清領與日治時期已累積了豐饒的文化土壤,它的文化力量是和經濟實力平行成長的。如果不是台灣這塊土地以同體大悲的襟懷消化流離苦難,我們很難相信一九四九來台的大陸因素如留在原有的土地,它可以躲過從反右到文革的一連串政治風暴。一九四九之所以奇妙,在於來自於大陸的因素結合島嶼原有的因素,產生了大陸與島嶼兩個個別地區都不曾觸及的、也始料未及的文化高度。 一九四九年的奇妙也在於此年歷史曾將枷鎖套在台灣身上,但台灣卻掙脫了枷鎖的束縛。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無從選擇地被納入國際冷戰體系,成為西太平洋上一艘不沉的特大號航空母艦,它的功能被設定了,它與世界的關係也改變了。海洋不再是黑格爾所說的交流之天然管道,而是成了森冷的海上柏林圍牆。舊大陸此時成了匪區,它是島嶼人民的對立面。新大陸則貶視台灣為反共體系中的一環,它僅能擁有工具的地位。台灣在文化意義上比在政治意義上更像是座孤島,台灣的新舊居民不得不在封鎖的孤島上,摸索自己的未來。由於物質條件不同了,居民組成的成分多樣化了。亞細亞的孤兒在生物學的孤島效應下,發展出異於舊台灣的自由經濟、民主制度、文化樣式與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世界非東非西,亦東亦西。它發展出比中國還中國,也比非中國還非中國的新華人文化面貌。 一九四九年發展出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顯然與十七、八世紀的傳教士或旅行家所見的華人社會面貌迥然不同,它不但是徹底的非舊台灣的,也是徹底的非舊中國的。在三個關鍵的象徵性年分中,一六六一年來台的明鄭王朝,能在政治上以區區島嶼抗衡大清,不可不謂是豪傑之舉。驅逐荷蘭此事在世界性的反帝抗爭中,尤具有指標的意義。但明鄭文化基本上是閩粵的區域文化,當時這一個區域文化總是受制於永不歇息的軍事行動,歷史沒有給它喘息以外的廣闊空間。一八九五年後的台灣子民能於異族專制下,借力使力,轉化「棄民」、「孤兒」的心境為奮進的動力,拓展開大幅的生存空間,其苦心孤詣不容後人不由衷感戴。但壓不扁的玫瑰雖壓不扁,其時的台灣子民不管在文化、生活或心理各種意義上都是附屬的,顯層的是附屬在扶桑島嶼,底層的是附屬在中原大地,台灣仍沒有成為啟蒙精神的子民。 從一六六一到一九四九,台灣這塊島嶼曾發生過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台人精神之奮發也是極可感的,但無庸諱言,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期間,台灣雖曾出現過不少優秀的學者、詩人、書家、畫師,但其作用基本上都是島內的,影響沒有波及全國。三百年的台灣極少出現過全國性的文化巨人,也沒有產生過全國性影響的學派、畫派、詩派、書派。沒有這些重要的文化指標並不意外,也不一定可惜,因為洪荒留此山川,原汁原味,它沒文明化,也沒有腐化。它的初步意義先是作為遺民與移民的世界,接著再累積創造力。從清領到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化天空雖缺少耀眼的巨星,但民間社會的文化能量並不比大陸大部分的地區少。它需要的是更進一步地找到表現的形式,它的火山精神仍在海洋底層醞釀,等待有朝一日迸破而出。 一九四九年就是台灣等待的契機,因緣成熟時,台灣這隻不馴的怒海鯤鯨終將遽化為沖天大鵬,翱翔於世界的長空。但人在此山中,山的真面目是看不清楚的。只有走過歷史,回首反省時,我們才不能不驚嘆此年歷史意義之重大,它竟然能催生這麼燦爛的台灣新面貌,我們看到了傳統文化最精緻的發展:我們發展出中國佛教史上最典型的人間佛教,我們發展出民國哲學史上最具創發力的新儒學,我們擁有從飲茶到戲劇極精緻的傳統文人文化,我們也擁有深厚的東方社會之工商管理模式,即使在流行的庶民文化領域,從飲食到流行歌曲,我們也看到了一股壓抑不住的衝動。如果要尋找台灣的「正統」文化,我們不難發現:它不存在於政治圈的法統,也不在光豔耀眼的牌樓、博物館或大人物的紀念館,而是滲透在每一生活細節中的文化氛圍。在文化意義上,台灣比任何華人地區更有資格代表漢文化,因為漢文化在這裡是生活中的有機成分,它仍在欣欣不已的創造。 一九四九年曾是個苦悶的年分,不管是舊居民或新移民,沒有人知道台灣下一步的命運為何。地理的前方是汪洋,地理的後方也是汪洋;歷史的過去是苦痛,歷史的未來好像也還是苦痛。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大家都在鬱悶中煎熬,也在迷惘中摸索。但歷史的目的是曲折的,歷史的意義超越了個人的意圖。苦悶的一九四九年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它的自我揚棄,一九四九的意義要在歷史走過一段路頭後,驀然回首,其豐饒的圖像才會經由苦痛的自我否定而顯現出來。蛻變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發生了,一種從一九四九長出的新興文化已是我們生活世界中最自然不過的氛圍,從飲食、語言到信仰,我們的社會早已有機的融合了藍海洋與黃土地的精粹。我們現在的一九四九轉化了歷史上的一九四九,一九四九需要經由後一九四九才能展現出它的本質,新的台灣就這樣被撞擊出來了。 一九四九的意義再怎麼宣揚都不會太過分,由於有了一九四九,我們的世界觀完全不一樣了。抽離了一九四九,我們的親友網脈就不完整了;抽離了一九四九,我們就缺少一塊足以和世界對話的宏闊背景。一九四九是個包容的象徵,隨著時間的流轉,以往建立在特定的語言、習俗、血緣上的舊論述不得不鬆綁,一九四九使得「台灣」、「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內涵產生了質的突破。每一位島嶼的子民都不再鬱卒,它們與島嶼相互定義,彼此互屬。 一個迥異於過去四百年的新台灣已經被撞擊出來了,但更重要的新台灣還在形構之中。台灣在中國大陸旁,在東亞世界中,台灣的地理位置曾使它歷盡了不堪的滄桑。但痛苦是成長最大的動力,台灣的存在應該有更高的目的。隨著中國與東方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興起,台灣會在歷史的新巨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這樣的歷史目的論不是玄想,而是台灣人民很謙卑的一種祈求。因為經由血淚證成的創造性轉化,中國與東亞不必然再是台灣外部的打壓力量,它們反而是台灣內部創造力的泉源。我們不因懷舊而回首,我們的回首是為了迎向未來,回顧的雙眼與前瞻的雙眼是同樣的一對眼睛。歷史會證明:一九四九是個奇妙的數字,台灣人民將它從苦痛的記憶轉化為傲人的記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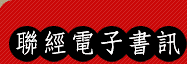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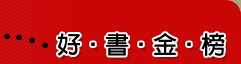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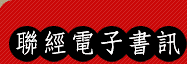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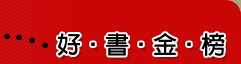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