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1891年首次踏上大溪地的土地後,他願意將自己今生最後的十二個年頭,都花費在這裡的氣候、景色和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之中。
什麼是野性和自然?什麼是藝術?什麼又是真正美好的生命?我們不知道高更是否在長年的思考中獲得自己認同的滿意答案,無論如何,我們能確定的是,大溪地的生活刺激了他的思考,反省文明帶來的束縛,激發了他潛在的生命力。
與大家分享高更自己整理他在大溪地生活時的日記《諾阿•諾阿》的內容,相信大家將會更加了解高更以及他留下的美好畫作。
▋高更在毛利部落的生活紀錄
文明慢慢地從我身上消退,我的思想也變得單純了。對鄰居們的怨恨現在所剩無幾;相反,我開始喜歡他們了。我的生活自由自在,既有動物性的一面,又有人性的一面,其中自有無窮的樂趣。我逃離了虛假與矯飾,進入自然之中。我堅信明天會和今天一樣,一樣自由,一樣美好。安寧降臨我的心中,我各方面一切正常,種種無謂的煩惱皆不復存在。
我交上了一個好朋友。是他主動找我,當然並無不純的動機。這是一個小夥子,住在附近,性格淳樸,長得也很精神。我那些五顏六色的畫,以及我在樹林裡作畫的情景,使他驚奇與困惑。他跑來問這問那,我的回答他似乎聽進去了,並有所領悟;於是,他每天都來看我畫畫或雕刻。
到了晚上,我不工作了,我們倆便聊起天來。年輕人名叫若特發,真是個小野人,歐洲人的事情什麼都想知道,特別是在愛情方面,他的問題常常使我不好意思啟齒作答。然而,他回答我的問題比向我提問還要天真。一天,我把工具遞給他,叫他也試著雕刻一件什麼東西。聽了我的話,他竟驚訝得愣住了,久久地望著我。最後才說,我跟別人不一樣,別人是不會像我這樣待人接物的。他說得樸實,絕無半點虛情假意。就我記憶所及,若特發是用這種語言同我講話的第一人。這是孩子的語言。是啊,除了孩子之外,誰還設想得出一個畫家幹的也是正事,也會有些用處⋯⋯。
一次,我需要一株玫瑰樹,雕刻一件什麼東西,樹幹要實心的,越粗越好,便求助於若特發。
……「那得到山裡去,」若特發回答道,「山裡有那麼個地方,我知道,有不少棵這種樹,長得又高又粗。我可以帶你去,想砍哪棵就砍哪棵,咱們倆把它拉回來。」
……
我們倆赤身露體,只在腰間圍著一塊布,手裡拿著斧頭,不時橫穿溪水,為的是利用對岸的一截小路。其實,哪裡有什麼路?如果有的話,肉眼是一點兒也看不出來的。空間裡無處不是草叢、樹葉、花朵,混雜中顯得壯麗輝煌。路,是我的夥伴用鼻子聞出來的。
寂靜,一片寂靜。亂石間流水單調的嗚咽,是伴奏,使寂靜更加完全,更加純粹。
在這美妙的榛莽裡,只有兩個人,活動於孤獨與寂寥之中。他,那麼年輕;我,幾乎是個小老頭,心靈裡凋謝過不知多少夢幻的花朵,身軀上留下了不知多少勞累的痕跡,另外還有個道德與身體都病入膏肓的社會遺傳給我種種源遠流長的邪惡與毛病。
他走在前面,身子像動物一般靈敏,各個部位都十分勻稱;從後面看上去,給我以集兩性於同體的感覺,似乎包圍著我們的植物界的壯美完全體現在他身上了。從他身上集中體現出來的這一壯美裡,揮發、擴散出一種美的芬芳,使我的心靈陶醉。在這芬芳裡,還混合著一種特別強烈的氣味:我倆之間相互吸引而產生的友情。這是單純物與複合物之間的吸引。
走在我前面的是個男人嗎?在這些不穿衣裳的部族裡,就和在動物群裡一樣,兩性間的外在區別並不像在我們的氣候條件下那麼明顯。我們突出了婦女的柔弱,看上去是使她們避免了勞累,實際上我們同時也剝奪了她們鍛煉與發展的機會。我們是按照一種崇尚纖弱的虛假理想來塑造女子形象的。
而在大溪地,森林與海洋的空氣給所有的人以強壯的肺葉、寬闊的肩膀和有力的雙腿。海灘上的卵石和天空中的太陽,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女人和男人幹一樣的活計,男人和女人一樣地慵倦與無憂無慮。女人都有雄渾與陽剛的一面,男人身上也不乏嫵媚的氣質。兩性間這種相似之處,給男女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便利。再加上大家都永遠赤裸著身體,這種關係更保持著一種完全純潔的性質。在他們的風俗裡,性愛根本沒有文明人那種羞羞答答與遮遮掩掩的情調。大家一覽無餘,沒有陌生的概念,沒有神祕感,誰也沒有特權,是男是女一個樣,誰也不佔便宜,誰也不受損害——本來我們文明人那套玩意兒就是遮羞布,是掩蓋性虐待狂的遮羞布。
既然在兩性外表區別不突出的「野蠻人」中,男女之間既是朋友又是情人,而且完全排除邪惡這一概念,為什麼此時此刻,這個文明之邦來的老傢伙,卻抵擋不住「陌生人」威望的誘惑,突然想到邪惡上面去了?——我湊了過去,太陽穴蹦蹦直跳。就我們兩個,沒有別人。我已經預感到了罪惡⋯⋯。
這時,路到了盡頭。我的夥伴打算橫過溪流到對岸去,便轉過身來,前胸朝著我,近在咫尺。
頃刻間,兩性人消失了。我面前站著個小夥子,一個年輕男子;眼神天真無邪,像平靜的水面,閃著明澈的亮光。
我跟著下到冰涼的溪水裡,寧靜頓時回到我的心田。我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快感:既是肉體的,又是心靈的。
「陶埃陶埃(真涼啊),」他對我說。
「噢!沒什麼。」我回答道。
這聲驚歎結束了我思想中剛剛進行的一場鬥爭,一場反對墮落了的文明鬥爭。一聲「噢」引出了山峰響亮的回聲。大自然理解我,大自然在傾聽我。現在,經過鬥爭,我勝利了,大自然便以洪亮的嗓門告訴我,它歡迎我,把我當成它的兒子。
我猛地鑽進灌木叢中,似乎希望與廣闊的大自然媽媽融合在一起。而我身邊的夥伴並沒有停下來,眼神還是那麼平和與寧靜。他什麼也沒有覺察到:我獨自肩負著壞思想的重荷。目的地終於到了。高聳的石壁在這裡形成一個喇叭口;越過一道茂密的林木屏障,裡面豁然開闊,竟是一片平地。平地上長著十來株大玫瑰樹,樹冠異常寬廣。我們選中一株最好的,掄起斧頭砍起來。要找一枝適合雕刻用的玫瑰木,非得把整棵樹砍倒不可。我使出渾身的力氣,掄起斧頭劈下去。幾斧頭過後,虎口震裂流出鮮血,然而,這時候我像發了狂,什麼也不管不顧了,似乎不這樣不足以壓住我內心那股來自神靈的暴怒。我砍的不是樹。我想砍的也不是樹。一棵樹砍倒在地後,我還不願停手,還希望聽到利斧敲擊其他樹幹的樂音。
隨著嘹亮的砍砸節奏,我似乎聽到斧頭對我吟唱:
砍啊,砍,把情欲的森林齊根砍倒, 乾乾淨淨,一棵也不剩。
砍啊,砍,把你心中的自愛自憐統統砍掉,
就像秋風裡,人們用手把蓮藕拔掉。
文明之邦的老頭被砍倒了,事實上,他真真切切地不存在了,他死了。我正在獲得新生,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我身上,一個純潔而強健的新人正在出生。這是場殘酷的衝擊,它可能導致與文明、與惡的最終告別。我覺得,在每個墮落的靈魂裡蟄伏著的道德敗壞的本能,一下子現出原形,無比的醜陋與惡劣,達到了與我剛剛獲得的清純壯美的光明分庭抗禮的程度。在這場旗鼓相當的對峙中,道德敗壞的本能沒有占上風,反而使我剛剛獲得的健康、淳樸的生活顯示出前所未見的魅力,這場內心的較量是決定我向哪邊倒的大搏鬥。而鬥爭的結果,我終於脫胎換骨,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野蠻人、毛利人。
在往回返的路上,若特發和我內心寧靜而欣慰,肩上扛著沉重的樹幹:諾阿,諾阿!
到達我的茅屋前,真是筋疲力盡了。這時,太陽還沒有落山。
若特發問我:
「你高興嗎?」
「當然。」
我內心深處不斷重複著:當然,當然⋯⋯我久久不願砍鑿這塊木頭。我聞了它不知多少次,一次比一次用力。這是勝利的芬芳,是返老還童的馨香。
本文內容參考自《諾阿•諾阿:你不可不知道的高更與大溪地手札》/華滋出版 ,保羅•高更
◆藝術家延伸閱讀:《西洋藝術便利貼》 / 《盡情瀏覽100位西洋畫家及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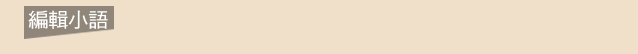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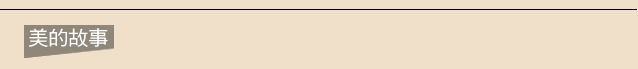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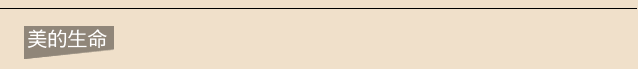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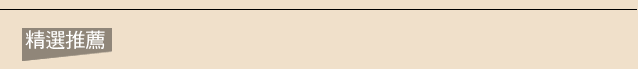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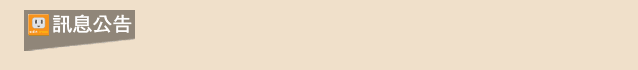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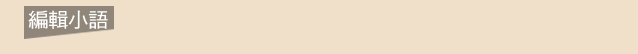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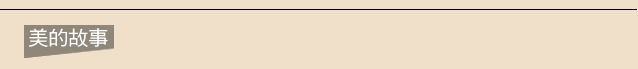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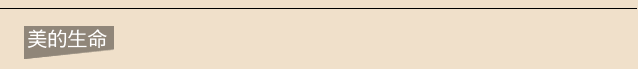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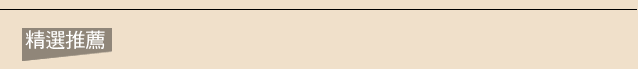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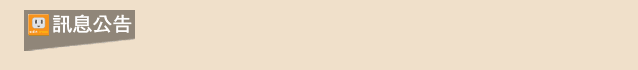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