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料共和國:從洋茴香到鬱金,打開A-Z的味覺秘語 從中世紀至今的香料史和廚房烹飪史!
香料,讓你身心和味蕾都歡欣鼓舞,為你勾勒世界的版圖! 埃及艷后為什麼以番紅花和馬奶沐浴?
十八世紀的苦艾酒為什麼會讓人充滿幻覺?
在遙遠印尼島嶼上收獲的丁香如何進入古敘利亞的廚房?
每一間廚房幾乎都含有一瓶丁香或幾根肉桂棒,
每一道菜都免不了加一點孜然或辣椒,
在約翰•歐康奈活色生香的說明中,你將津津有味地消化香料大餐。 ※ ※ ※ 導言(節錄)
法國的亞述文化專家尚•布泰羅(Jean Bottéro)解譯出三塊破黏土板上約西元17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使用的阿卡德(Akkadian)文字,他發現這其中不但有舉世現存最古老的食譜,而且這些食譜十分複雜,證明了當時已有科學根據的烹飪方法,讓原本以為當時人類只會把豆類煮成一團爛糊的他和同僚大吃一驚。他收集整理這些食譜,出了《舉世最古老的料理:美索不達米亞的烹飪》(The Oldest Cuisine in the World: Cooking in Mesopotamia,2004)一書,其中就包括原始的咖哩菜餚,羊、山羊、鴿子、公鹿和鷓鴣等肉類用火炙燒至焦黃,然後浸在油膩的香料肉湯裡煮。作家兼美食部落格主蘿拉•凱利〔Laura Kelley,又名絲路美食家(The Silk Road Gourmet)〕,就以布泰羅的書為本,自行研究,結論是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蘇美人可能已會運用各種香料,包括肉桂、甘草、角豆、蒔蘿子、杜松、鹽膚木、孜然,和阿魏。 我想要說明很簡單而且本書也會不斷印證的一點:飲食習慣的改變並不是一板一眼循序漸進,沒有人想要、而且也不能夠監督管理,這些改變是出於意外,尤其是來自同化。兒時吃坦都里雞的驚艷印象,對我日後三十年的味蕾產生了作用,經由蜿蜒的味覺幽徑網路,影響我的烹飪和我想吃的食物。簡言之,它讓我愛上了辛香的食物。 食物一如語言:不斷的變動是常態,想要以嚴格的規則分門別類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現實世界裡,食譜就是以偶然而不經意的方式四處傳播。 當然,跨國旅遊、移民,和網路的盛行,使這個過程更如火如荼展開。比如上週我想要把剩下的一些梅子用掉,因此翻閱國家信託協會(National Trust) 出的食譜,決定做一道中世紀晚期的古法燉羊肉。我讀了食譜,覺得如果用爪哇的畢澄茄或非洲的馬拉奎塔胡椒(melegueta pepper,天堂子)取代黑胡椒,滋味會更好,可是我去本地的森寶利(Sainsbury’s,英國第二大連鎖超市)卻找不到──真教人意外!可是到倫敦南區非洲-加勒比海裔社區中心的布瑞斯通市集(Brixton Market),卻得來全不費工夫,而且就算找不到,網購也一定很簡單。 如今我們把香料視為理所當然,處處可見,而且賤如塵土,但其實香料可說是自古以來最重要的商品──比石油和黃金都還重要。歷史曾把它們視為聖物,儘管就飲食的本質來說,它們根本並非必要。 從沒有人因為缺乏香料而死,但卻有成千上萬的人──包括掠奪者和受害者為它而死。因為控制豆蔻、肉桂、丁香和黑胡椒等重要香料交易而產生的私欲,使歐洲的商業強權犯下許多和目前在中東動盪地區所見相似的暴行。
然而,要是沒有香料貿易帶來的財富,恐怕根本不會發生文藝復興。大仲馬在描寫威尼斯時,把這點說得十分透徹:「在香料刺激造成的興奮影響之下,智能的表現達到高峰。提香的畫作是否香料的功勞?我忍不住要這麼想。」(十五世紀末時,威尼斯每年由亞歷山卓進口50萬公斤的胡椒,不過後來數百年,鄂圖曼帝國限制威尼斯與敘利亞、埃及的交易,香料對威尼斯繁榮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所有重要的探險告訴我們世界是怎麼構成的,由故事書中傳奇人物如哥倫布(在西班牙君主贊助下4度橫渡大西洋的義大利人)、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史上第一位由歐洲航海到印度的人)和同為葡萄牙人的麥哲倫(他航行至東印度群島,完成地球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全都免不了出於貪婪,想要找出香料生長的地方,省掉掮客──在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販售香料的阿拉伯和腓尼基商人們。 在達伽馬之前,香料沿著各種商隊路徑來到歐洲,不是越過中東,就是繞著紅海來到埃及,並沒有獨一無二的「香料路徑」。它們的起源是印度、斯里蘭卡、中國和印尼。有些香料,比如豆蔻和丁香,生在遙遠而狹小的島上,地圖上沒有標記出〔豆蔻產於西太平洋的班達群島(the Bandas);丁香則生在摩鹿加群島(Moluccas Islands,今Maluku,馬魯古)〕,只能由這些島上取得。然而一旦建立了海上航路,填滿了地圖上的空白之後,香料就由歐洲直接掌握,各國也成立了龐大的企業,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荷蘭的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負責香料的交易,並統治香料植物生長的土地。然而當香料開始在非原生地培養種植之後,這些大企業的壟斷也就瓦解。 不過或許在進一步往下讀之前,我們該先為我們的詞彙下個定義。究竟香料是什麼?英文spice這個字源自拉丁文specie,意思是「種類、類別、類型」,和‘special’(特別 )、‘especially’(尤其)和‘species’(物種)同樣的字根。在我看來,此字最佳的現代定義是史學家傑克•特納(Jack Turner)在《香料傳奇》(Spice: The History of a Temptation)一書中所說的:「廣義來說,香料並非香草植物,香草是公認有香味草本植物的綠色部份,香草植物有葉子,而香料卻是由植物其他部位取得的:樹皮、根、花苞、樹膠和樹脂、種子、果實,或花柱的柱頭。」但另一位在香料界鑽研多年的權威,美國作家菲德列克•羅森嘉頓(Frederic Rosengarten)則主張:「很難分辨香料和香草植物,因為烹飪用的香草植物其實就是一組香料。」 香料的故事是屬於全球的,一路走來,在印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埃及、伊朗、伊拉克、中國、俄羅斯和馬達加斯加都有站要停,但也不要忘記新世界的南北美洲、北歐、中歐和東歐,以及英國。德高望重的食物史學者安德魯•道比(Andrew Dalby)認為這也影響香料的定義:香料是「生在遙遠的地方,經由長距離的貿易而得,並且有獨特的香氣」;是「來自單一有限地區的天然產物,需求殷切,價格高昂,人們為其風味和香氣所願付的價錢,遠超過原產地的價格」。大多時候,尤其是古代,香料常作為藥用,而非為添加食物的風味──也用在塗油儀式,或者當香水和化妝品。但道比也指出,食物和藥物之間的區隔往往很模糊。 結果演變成,在中世紀,「香料」往往是指昂貴的進口物品,因此除了肉桂、豆蔻、黑胡椒之外,這個詞還包括了杏仁、柳橙、龍涎香(抹香鯨消化系統所分泌的蠟狀物質,用來製造香水)和各種染料、油膏、和醫藥物質,如作為藥用的木乃伊屍體,或者由亞歷山卓的煙囪刮下來的屑屑,製成膏藥,用來敷在皮膚潰爛上。如今我們認為香料可食,而像乳香(frankincense)和甘松香(spikenard),則是不可食的芳療藥物,但其實從前卻把這些「可食」的香料當作焚燒用香:據說羅馬暴君尼祿在第二任妻子死亡之時, 就把全城的肉桂都付之一炬。 《中世紀廚房》(The Medieval Kitchen,1998)一書的幾位作者寫道:「追根究柢,中世紀的廚師是煉金術士──只是他追求的不是黃金,而是色彩。」而且中世紀對香料的狂熱並非歐洲獨有的現象:十四世紀初,蒙古帝國的御廚在大都(北京)烹飪時就用了24種不同的香料。 大部份的食物史學家都主張,阿拉伯料理對歐洲中上階層的烹調方式影響深遠,羅森嘉頓就認為十字軍東征刺激了貿易,使得從聖地來的進口商品「空前豐富」:「椰棗、無花果、葡萄乾、杏仁、檸檬、柳橙、糖、 米,和形形色色的東方香料,包括胡椒、豆蔻、丁香和綠豆蔻」。但也有人提出異議:克利佛德•萊特(Clifford A. Wright) 認為:「十字軍對西方歐洲理並無影響」,因為「義大利商人當時已主宰東方,伊斯蘭政權也掌控西班牙和西西里,因此早就發生了文化接觸。」 歷史學者查爾斯•孔恩 (Charles Corn)寫道,香料喚起了「即使不算神話也可說是傳奇的連續事件,是紮根於古代的故事」。中國和阿拉伯商人在西元六 、七世紀時就已經在摩鹿加群島做起香料生意,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挖掘出的遺物也發現:早在西元前3300年至1300年之間,人類就已經會使用香料:在印度北部哈里亞納邦古城法瑪納(Farmana)的磁器,和葬在當地的骨骸齒縫中,都有薑和薑黃的遺跡。 內文選摘(節錄) 孜然(Cumin)
Cumimum cyminum 
就影響和普及這兩方面來看,1生小型草本植物小茴香的乾燥種子小茴香子,別稱孜然,是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它有強烈且持久的檸檬和紅糖香味,在許多國家市售和自製的咖哩粉中,都是主要成份,如波斯的阿德魏(advieh)、阿富汗的恰馬薩拉、中東的巴哈拉特、印度的格蘭馬薩拉,和北非的醃漬醬(chermoula,摩洛哥青醬)等混合香料。在歐洲,它的主要用途則只限於印度甜酸醬和德國酸菜,不過萊頓(Leyden)和高達(Gouda)等荷蘭起司也有添加孜然,另外如果以阿爾薩斯的芒斯特(Munster)起司配麵包,也會撒一點在上面食用。 伊麗莎白•大衛告訴我們說,孜然溫韾的芳香「瀰漫著北非和埃及的露天市場,讓摩洛哥的燒烤羊肉串有它獨特的風味,也出現在地中海東部種種蔬菜、肉類和米飯的菜色中。」乾煎孜然可以帶出它堅果的香味,並緩和磨成粉會有的苦味。 孜然如果加在肉類,和羊肉最搭調;如果配蔬菜,則與胡蘿蔔相合(比如摩洛哥經典的生胡蘿蔔、大蒜和孜然沙拉),更教人吃驚的是,它和甜菜根也很速配:《河邊小屋每日青菜食譜!》(2011)的作者休•芬姆利-威丁史塔(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就步古老食譜阿皮基烏斯《烹飪技法》的後塵,用甜菜根、胡桃和孜然的天然組合,達到了泥土甜美和溫暖的完美平衡。該不該加鷹嘴豆泥,大家莫衷一是,其討論的熱烈程度唯有鷹嘴豆泥是由阿拉伯人抑或猶太人發明差堪比擬。 …… 孜然在埃及土生土長,是使用在葬禮塗香膏儀式中的諸多香料之一。在伊朗、土耳其、印度(舉世最大的香料生產及消費國)、中國、日本、美國和如索馬利亞和蘇丹等非洲國家都有栽植。它生有紫白色的花朵和嬌弱的莖,因此匐匍蔓延。它毛茸茸的錐形種子長3-6毫米,有成對或分開的心皮(carpels)。它們的長得很像葛縷子的種子,因此造成各種烹飪和字源的混亂──印度文兩者都用jeera表示,德文則用kummel代表葛縷子和孜然味的酒。更細緻的伊朗黑孜然Bunium bulbocastanum常被誤認為黑種草(nigella)。孜然需要像打穀那樣脫粒;泰奧弗拉斯托斯說,這種植物「在播種時一定要詛咒和虐待,收成才會漂亮且豐富」。如果做得恰當,孜然就會生出「比任何植物都多的果實」。 …… 普林尼對孜然從不厭煩──在其他調味料顯得平淡之時,「永遠都歡迎」加一點孜然。在古代的羅馬,到處都可看得到孜然:磨成糊好加在麵包上,或者和鹽混合,製成孜然鹽,迄今在北非依舊流行。 阿皮基烏斯把孜然用在上百道食譜裡,包括搭配牡蠣和貝類的醬汁,這或許讓你以為它很昂貴,但其實它賤如塵土;比胡椒便宜。古希臘把守財奴稱為 kyminopristes,字面上的意思是「劈開小茴香子的人」。據說古羅馬哲學家皇帝馬可•奧里略(著有《沉思錄》)因為節儉小氣,而被取了「孜然」這個綽號。不過在德國,孜然代表的是忠實:新娘在婚禮上捧著孜然、鹽和蒔蘿,表示發誓忠實於丈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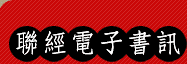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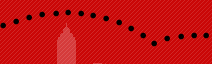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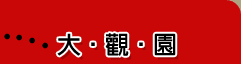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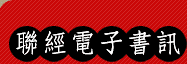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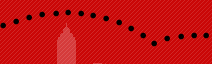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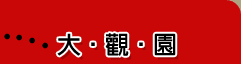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