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師變記者,只為拍一張能改變某個人日常生活的照片!】 能改變某個人日常生活的一張照片
攝影記者 宋美兒
反映世界的緊迫感
在漆黑的山裡像瘋子一樣狂奔的時候,宋美兒的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一定要趕在凌晨之前發出去」。遠處轟鳴著槍聲和炮聲,每當這個時候她只是把方向盤握地更緊。疾馳一陣子後,她終於到達了山頂。她把衛星電話舉到空中,等待電話響應人工衛星的信號,可是卻沒有應答。經過昨晚焦灼難耐的奮戰,第二天早上,她拍攝的照片透過報紙向全世界呈現了海地的慘狀。宋美兒在全世界的危急現場取材,採訪了無數美國的重大事件。她是美國《明星紀事報》(The Star-Ledger)歷史上唯一來自韓國的攝影記者。
宋美兒擁有華麗的履歷,她曾獲得授予本年度最佳報紙、電視記者的權威大獎─雪梨. 希爾曼基金會獎(The Sidney Hillman Foundation),並且獲得了身為記者的最高榮譽─凱西獎(Casey Medals)。她畢業於韓國中央大學攝影系,在俄亥俄大學研究所進修新聞攝影,後來她進入《明星紀事報》報社,二○○四年在內戰正酣的海地發出了記者生涯的第一篇新聞報導。  妳作為攝影記者踏出的第一步就是去海地,一定很不容易吧。
加入《明星紀事報》沒多久的時候,某天晚上我接到了報社的電話,讓我立刻出發去海地。當時海地遭到暴雨侵襲,整個國家遭受洪澇災害。我連行李都來不及整理,去報社領取了差旅費就匆匆趕到了機場。因為海地正值內戰,沒辦法直接入境,我們只能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借了車從陸路進入海地。到達海地的時候,天氣很糟糕,暴雨侵襲村莊,有的村莊因為山體滑坡瞬間就被掩埋,當地居民們很擔心會爆發傳染病,都極度不安。
因為當時正值戰時,誰也不知道狀況會如何發展。雪上加霜的是,記者拒絕去戰爭現場取材。我堅持一定要去現場。最後,我自己一個人經歷一番曲折後終於拍到了照片、完成取材,傳送了報導。所以我首次負責的國際報導中,我的名字和照片一起刊在記者行列中。  取材的時候,最辛苦的是哪一點?
在當地最令我焦慮的事情,就是傳送照片。雖然現在到處都有網路,但當時我們都是用衛星電話,有很多限制。有一次完全沒有信號,我開車尋找能捕捉到信號的地方,自己一個人跑到了山裡。但是我熬了整整一夜還是沒有捕捉到信號,都快急死了。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了能上網的地方,傳送完照片後,整個人都累癱了。
不僅如此,到了預定離開的那天,我們卻聯絡不到約好來載採訪團的直升機,整個採訪團都被困在那裡。當時,美國派遣美軍幫助政府軍壓制叛軍。報社指示我們利用被困住的這段時間,採訪海地當時的政治狀況。正好我們可以從一名當地嚮導那裡獲得叛軍地區的情報。聽到這句話的瞬間,我心想一定要去叛軍地區看看。我認為叛軍的做法都是有原因的,讓大家也了解他們的立場才算公平。更重要的是,有一種本能在驅使著我。我到了叛軍地區,偶爾可以看到拿槍的人。雖然他們反美情緒很強烈,但人們都意外地友好。媒體報導中的叛軍是「邪惡軸心」,但在我看來,他們只是平凡的村民。
我取材結束後回來,採訪團出現了騷動。其他記者向美國方面打電話報告說我失蹤了。整個報社因此進入緊急狀態,我花了一番工夫才讓事情平息下來。
取材的時候,我們也曾去過連電都沒有的偏僻村子,整個村子都被暴雨摧毀,村民們就生活在空蕩蕩的土地上。他們失去了家人和朋友,渾渾噩噩地活著。取材結束後回去的時候,那裡的村民紛紛塞給我們一張張紙條。打開紙條一看,裡面寫著一個個名字。他們把希望寄託在外來人身上,把心願寄託在寫離散家人名字的紙條上。他們那清澈的眼神,我至今都難以忘記。
「不知道他們現在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宋美兒的言語中透露著擔憂,眼神中蘊藏著憐憫。在慘不忍睹的第一次取材現場,她甚至和同行的記者發生衝突,在取材期間常常展開看不見的戰爭。同行的記者不願意住在斷水的旅館,因此他們不得不花了兩個小時尋找其他住處;第二天記者以安全的理由不願去現場,於是她獨自一人大膽地去取材。因為她有攝影記者的使命感,即使在內戰的緊張感達到極致的狀況下,不管什麼原因她都必須奔赴現場。她的照相機如實反映了海地當時的狀況。  科學老師宋美兒,人生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攝影記者宋美兒曾經是在國中教科學課的老師。當我說「這兩項工作一點關係也沒有嘛」的時候,她笑著說,雖然從大學時起她就對攝影很感興趣,但因為搞學生運動,根本沒時間學習。她在大學念的是化學教育學系,她也很喜歡教小朋友,但反覆地教同樣的內容令她對生活感到厭倦。當時她出於興趣學習的攝影改變了她的人生。
本文摘自《像他們一樣工作:紐約人的生存白皮書,向他們學習熱情、創意、成長》
>>>想看更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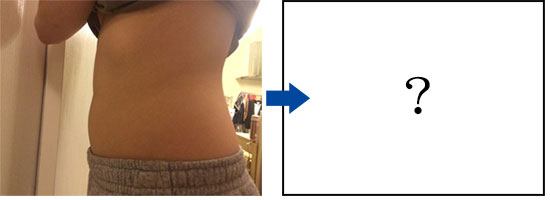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