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
前言
停滯狀態 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有兩段文字鮮少被人引用,其中他提及了一種「停滯狀態」:原本富有的國家不再成長的狀態。這一狀態的特點為何?亞當•斯密特別指出該狀態的社會退化特徵。首先,超過半數的人工資低得可憐: 一國儘管非常富裕,但如果長期停滯不前,絕無指望工資會很高……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最幸福、安樂的時候,似乎不是社會達到絕頂富裕時,而是社會處於進步狀態、正日益富裕時。停滯狀態下,生活艱苦;衰退狀態下,處境悲慘。進步狀態其實是社會各階級快樂、充滿活力的狀態。停滯狀態沉悶,而衰退狀態令人沮喪。 停滯狀態的第二個表徵,乃是腐敗、壟斷利益的菁英能利用法律和行政體系為自己牟利: 在富人或大資本家享有很大程度的安全保障,而窮人或小資本家不但安全保障不足,且隨時可能被下級官吏假正義之名掠奪的國家,投入國內各行各業的資金,絕不可能及於該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許的數量。在各種行業中,窮人受壓迫,必然造就富人的壟斷地位。藉由把持整個行業,富人將能獲致極大利潤。 我想,西方讀者思索這兩段文字時,在承認之餘,不可能不感到一絲不安。當然,亞當•斯密在世時,已「停滯良久」的國家是中國:一個曾經「富裕」但已不再成長的國家。亞當•斯密把中國的停滯不前歸咎於該國不健全的「法律和建制」—包括中國的官僚組織。欲矯正中國的停滯,他開出了藥方:更自由的貿易、更加鼓勵小企業、減少官僚作風和改正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作風。他親眼見到十八世紀晚期這類改革如何提振不列顛群島和其美洲殖民地的經濟。如今,相對的,如果亞當•斯密能重遊上述地方,將見到風水大翻轉。如今處於停滯狀態者是我們西方人,中國則以世上其他主要經濟體所不及的速度快速成長。經濟史走到這裡,主客易位,情勢逆轉。 本書談西方社會發展陷入停滯狀態的原因。亞當•斯密的洞見—停滯和成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法律與建制」的產物—是本書的靈感來源。本書的中心思想:亞當•斯密在世時用在中國身上十分貼切的陳述,如今用在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區同樣貼切。問題癥結在西方的法律和建制。始於二○○八年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只是更深遠的「大退化」(Great Degeneration)的一個表徵。 四個黑盒子 欲證明西方建制(institution)的確已退化,我得打開幾個闔上已久的黑盒子。第一個黑盒子名叫「民主」,第二個是「資本主義」,第三個是「法治」,第四個是「公民社會」。這四者同是構成西方文明的主要元件。我想讓大家知道,在這些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的黑盒子裡,存在極複雜的幾組環環相扣的建制。一如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運作的是裝置於內部的電路板,使這一精巧事物運作的則是這些建制。如果它停止運作,很可能是因為建制線路出了問題。光是檢視絢麗的外殼,無法得知哪裡出毛病,得檢視內部才行。 立法、司法與行政三者的相對關係為何?大部分憲法予以明訂。但文官機關與軍方的關係為何?在埃及這是極重要的問題。光釐清這問題也還不夠,現代民族國家已發展出一整套在一百年前還難以想像的建制,用以規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重分配所得。福利國不是古雅典人心目中的民主的一部分。以蜜蜂組織來比喻,福利國似乎創造出愈來愈多不事生產、靠工蜂來養活的雄蜂。福利國也僱用了許多只負責將資源從工蜂轉移到雄蜂身上的蜜蜂。而且福利國致力於以公債形式預支未來,藉以籌得自身所需資金。在第一章,我會探討此事和民主體制的其他分配層面。特別重要的是,我會探討柏克(Edmund Burke)所謂的世代間夥伴關係,是否正在我們眼前從根本上崩潰。 近來,幾乎人人都說自己民主。我甚至聽到有人說中國共產黨民主。相對的,「資本家」一詞常被用來辱罵他人,因而鮮少在上流社會裡聽到。民主國家的建制和市場經濟的建制彼此關係為何?企業透過遊說人士和競選獻金積極參與政治?政府透過補貼、關稅和其他扭曲市場的工具,或透過管制積極參與經濟生活?經濟自由與政府管制之間的平衡該如何拿捏才得宜?第二章會處理這些問題。我所要探明的問題,乃是非常複雜的管制本身已在多大程度上反倒成為它所宣稱要整治的那個疾病,扭曲、腐化了政治和經濟過程。 法治是使政治、經濟的參與者無法為所欲為的重要建制性機制。在健全的司法體系下,立法機構所制訂的規則能得到執行,個別公民的權利能得到維護,公民與法人實體間的糾紛也才能以平和、理性的方式解決。若缺少健全的司法體系,不管是民主還是資本主義,都不可能順利運行。但哪種法律體系較佳?普通法或其他?以伊斯蘭律法為圭臬的法治,顯然大不同於英格蘭政治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所理解的那種法治。 從某些方面來說,比較不同法典的關鍵在於「法規之法」,也就是制訂法律的方式。在某些體系裡,例如在伊斯蘭律法裡,規則由一神啟的先知詳訂,永世不易。根據較嚴格的穆斯林學派,這些規則不得更易。在其他體系裡,例如英格蘭的普通法裡,規則隨著法官仔細評量相對立的判例和變遷的社會需要,而有機地演變。第三章會探討一種法律體系(特別是普通法)是否優於別種法律體系的問題。我也會探討英語系世界在這方面仍享有多大優勢。特別是我想提醒讀者,法治有淪為較類似律師治理(rule of lawyers)的情況之虞,至少在「英語圈」某些地方是如此。美國人得自法律體系的服務,真的優於狄更斯《荒涼山莊》那個時代的英格蘭人嗎? 最後是公民社會。貼切的說,這是協會(公民為私利以外的目標成立的機構)當道的領域。這些機構從學校(儘管在近現代,大部分教育機構已被吸納入政治領域)到專門從事各種人類活動(從航空學到動物學)的社團,不一而足。在此,我們再度見到規則的重要性,儘管規則可能讓人覺得繁瑣,例如倫敦大部分社團要求會員在晚宴上打領帶、穿西裝外套,即使天氣悶熱也不例外。 曾有一段時期,一般英國人或美國人所擁有的社團和其他志願性協會的會員身分多得嚇人,那是英語系世界令法國知名政治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印象最深刻的特色之一。但在第四章,我將探討為何那已成為昨日黃花?當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活躍公民社會付之闕如後,真正自由的社會能發展茁壯到什麼程度?透過網際網路建構的新社會網絡能取代傳統協會式的生活嗎?我對此表示否定。 第一章 蜂巢社會 解釋大分流 「自然……是很有威力、很有功效的事物,但建制,亦即人為作為,力量更大得多,能修補、改造、強化歪曲且邪惡的自然,將其轉變為好的自然。」英格蘭人文主義者塔佛納(Richard Taverner)在其著作《智慧園》(Garden of Wysdome)中如此寫道。這番話扼要說明了那個正迅速成為有力共識的觀念:建制──最廣義的建制,比氣候、地理、乃至疾病發生率之類自然力量,對近現代歷史結果更具決定性。 為何自西元一五○○年之後,西方文明─一如在歐亞大陸西部那些好爭吵的小國和它們在美洲的殖民地裡所見,表現得比其他文明好上許多?從一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晚期,全球生活水平有驚人的分流現象,西方的富裕程度變得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地方。近至三百年前,一般中國人仍大概比一般北美人稍稍富裕。到了一九七八年,一般美國人的富裕程度至少是一般中國人的二十二倍之多)。歷史上的大分流不只見於經濟,從壽命、健康的角度看,也有分流現象。晚至一九六○年,中國的預期壽命仍只有四十歲出頭,而美國已達到七十歲。西方人主宰科學領域和流行文化領域。西方人建立了大約十二個正式帝國,在它們鼎盛時期,版圖涵蓋全球陸地面積和人口將近六成,經濟產出占全球經濟產出至少四分之三。而即使在這些帝國灰飛煙滅之後,西方人仍繼續以驚人程度支配世界。把蘇聯帝國稱作「東方」,乃是牽強的冷戰用語;蘇聯帝國其實是最後一個統治亞洲大片地區的歐洲帝國。 這一全球性失衡,使少數人──頂多五分之一──在物質豐饒程度和政治地位上凌駕於他人之上;而面對這現象,我們該如何解釋?十九、二十世紀的種族理論者,常主張這是歐洲人的某種固有優越性所致,但此說看來說不通。西元五○○年,歐亞大陸西陲進入為期將近一千年的相對停滯期時,基因庫肯定和那一千年後差異不大。同樣的,一五○○年時歐洲的氣候、地形、天然資源,和五○○年時也差不多。整個黑暗時期和中世紀,歐洲文明看不出有比東方諸大帝國更勝一籌的明顯跡象。我無意冒犯戴蒙(Jared Diamond),但地理和其對農業的影響或許可說明為何歐亞大陸比世界其他地方表現更出色,卻無法說明為何西元一五○○年後歐亞大陸西陲的表現比東陲好上那麼多。 從帝國主義的角度,我們也無法解釋這一大分流現象;歐洲人開始遠渡重洋、征服異地之前,其他文明就有許多帝國主義擴張行徑。創造「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詞的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認為,那其實只是運氣使然。歐洲人運氣好,無意間發現加勒比海地區的「鬼田」(ghost acres),而這些「鬼田」不久後就提供大西洋彼岸宗主國人民大量的糖—大部分亞洲人無緣享用,小巧不占空間的熱量來源。歐洲人也很幸運,擁有較易開採的煤礦床。但這觀點未解釋為何中國人沒有像歐洲人那樣努力出海尋找殖民鬼田,為何中國人沒能像英國人那樣解決挖煤的技術難題。 關於大分流的肇因,我深信最佳的答案要在建制上尋得,例如諾爾思(Douglass North)、沃利斯(John Wallis)及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看出人類組織有兩階段或兩模式的差異。第一階段是他們所謂的自然狀態或「有限制進入模式」(limited access pattern),其特點是: •經濟成長緩慢;
•非國有組織數量較少;
•政府小而集權,且在未獲被統治者同意下運作;
•社會關係根據個人原則或王朝原則組成。 第二是「開放進入模式」(open access pattern),其特點為: •經濟成長較快;
•富裕、充滿活力、具有許多組織的公民社會;
•較大、較地方分權的政府;
•社會關係受非個人力量規範,例如與財產權保障、公正、公平(至少理論上如此)相關的法治,就是這類力量之一。 根據他們的陳述,以英格蘭為首的西歐諸國,是最早從「有限制進入」過渡到「開放進入」的國家。為完成這過渡,國家須「制定相應制度,使菁英階層有機會建立非個人的菁英間關係」,然後得「創造出鼓勵菁英打開進入菁英階層之門的新誘因,並維持這些新誘因。」這時,「菁英把他們的個人特權轉化為非個人權利。所有菁英被賦予建構組織的權利……到那時候,邏輯關係……已從透過特權創造租金的自然狀態邏輯,變成透過進入權削弱租金的開放進入邏輯。」 從「諾曼征服」到光榮革命這期間,英格蘭從「脆弱」的自然狀態,演變為「基礎」狀態,再演變為「成熟狀態」;而「成熟狀態」的特點是具有「一大套指導、管理和執行土地產權的建制,且這些土地產權能支持菁英間的非個人交換。」對菁英來說,法治是過渡到開放進入體系之前的三個「入口條件」之一,另兩個是「公私領域裡常設組織」的出現和「對軍隊的牢牢掌控」。對諾爾思、沃利斯及溫加斯特來說,往開放進入體系的關鍵性突破,隨著美國、法國革命的爆發而降臨。這兩場革命期間,出現不同形態的社團,以及經濟、政治二領域裡公開競爭的正當化。在這一論證的每個階段,他們都把重點放在建制上,最初著墨於十一世紀後英格蘭土地法上的改變,最終著墨於十九世紀法人實體在法律上所受待遇的變化。 基於類似的思維,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把「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組成部分」界定為「強大的國家、國家對法治的服從,以及政府能接受全體公民的問責」。這三個要素首度聚合是在西歐,而英格蘭再度扮演開路先鋒(儘管福山認為荷蘭、丹麥和瑞典在這方面的表現也不遑多讓,因而讚許了這三國)。為何是歐洲,而非亞洲?因為,在福山看來,西方基督教世界自成一格的發展,往往削弱了大家族或氏族的重要性。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im Robinson)也對今日埃及和十七世紀晚期英格蘭做了鮮明對比: 英國比埃及富裕的原因,在於一六八八年……英格蘭……發生了一場使該國政治改頭換面,進而使該國經濟改頭換面的革命。人民爭取並贏得更多政治權利,利用這些權 利擴大自己的經濟機會。結果就是出現一個根本上不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過程,且這過程在工業革命中達到高潮。 用這兩位作者的話說,英格蘭是第一個得以擁有「包容性」或「多元性」政治建制,而未走上「榨取性」政治建制的國家。別忘了,其他西歐社會,例如西班牙,未能做到這點。因此,歐洲人在北美、南美兩地的殖民結果大不相同。英格蘭人輸出包容性建制;西班牙人滿足於將榨取性建制強加在他們從阿茲特克人、印加人接管的建制之上。 帝國背景也揭露了這一建制觀點與韋伯(Max Weber)首先提出,後來由蘭德斯(David Landes)修正的文化詮釋(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有某種關聯)之間的差異。與約斯特(Hanns Johst)劇作《施拉格特》(Schlageter)中那位納粹黨人不同的是,我不會一聽到世界文化這字眼就伸手去掏我的左輪手槍,但我的確發出委婉的告誡。人們傾向把歷史推手歸於觀念與準則的和合—希臘哲學、希伯來十誡、羅馬法、基督的道德準則、路德宗和喀爾文宗的教義,即所謂的「猶太-基督教文化」。但這有可能失之偏頗。真正駭人的西方觀念,例如燒死女巫或共產主義,從頭至尾未被提及,但它們似乎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樣稱得上是猶太-基督教文化的產物。無論如何,文化會把準則灌輸於人,潛移默化影響規則,建制則創造誘因。同樣是英國人,接受一樣的文化,卻因移民到新英格蘭或赴孟加拉為東印度公司工作的不同選擇,而有大不相同的行為表現。在前一情況裡,我們找到包容性建制,在後一情況裡,則找到榨取性建制。 光榮建制 大分流肇因的辯論,不只攸關歷史真相的探明。了解西方的成就,有助於我們擬出關於晚近歷史、現在、可能還有未來的一些更迫切的提問。建制論點之所以令人難以反駁,原因之一在於它似乎也為大部分非西方國家直到二十世紀晚期才實現經濟持續成長一事,提供了有力的解釋。艾塞默魯和羅賓森描述了城區被美墨邊界切成兩半的諾加利斯市(Nogales),藉此說明建制相對於地理環境和文化所擁有的力量。兩城區生活水平的差異大得驚人。同樣的道理用在冷戰期間的兩場重大實驗上也很貼切。韓國和德國這兩個民族都被一分為二。南韓人和西德人擁有基本上屬於資本主義的建制;北韓人和東德人則擁有共產主義建制。短短幾十年,就出現明顯的分流。對這兩個例子的分析,使艾塞默魯和羅賓森懷疑中國尚未完成通往永續成長的關鍵性突破。他們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仍受制於排他性、榨取性菁英的決定,關鍵資源的分配仍由這些菁英來決定。 發展經濟學家,特別是科利爾(Paul Collier),思考這些問題已有一段時間。波札納的例子似乎闡明,就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經濟體,只要其人民未受長期腐敗之苦或剛果民主共和國之類的內戰侵擾,也能獲得持續成長。與大部分後殖民時期非洲國家不同的是,波札納如願獨立時,成功建立了包容性而非榨取性建制。祕魯經濟學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多年來也一直主張建制是重要關鍵。他和研究人員不辭艱辛,走過利馬、太子港、開羅和馬尼拉的貧民區,證實窮人儘管收入不豐,擁有的財產卻多得出人意料。問題癥結在於法律未承認這財產是他們所有。這財產幾乎全是「非法定」持有。這不是因為窮人逃稅。誠如德索托所闡明的,地下經濟有自己的課稅方式(像是保護費之類的),而這種課稅方式使合法性成為追求的標的。其實,純粹是因為他們幾乎不可能取得房屋或工作坊的合法所有權。 為實地了解,德索托和其研究團隊依照法律程序申請在利馬郊區成立一間小型成衣工作坊,結果花了兩百八十九天才如願。而他們申請在國有地蓋一棟房子時,花了更長時間,共六年十一個月才得到批准。在這將近七年期間,他們得和五十二個政府機關打交道。德索托主張,像這類效能不彰的建制,乃是迫使窮人遊走在法律之外的原因。切勿認為地下經濟微不足道。德索托《資本的奧祕》一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發現之一,乃是開發中國家窮人所持有(但非合法擁有)的不動產總值達到九.三兆美元。但由於缺乏合法所有權和健全的財產法體系,這全是「未受法律承認的資本」(dead capital):「就像安地斯高山湖泊的水—未開發的潛在能源庫。」這一資本無法被有效率地用於生財。只有具備健全的產權體系,房子才能成為擔保品,才能被市場確立其應有價值,也才能輕鬆買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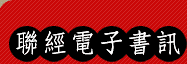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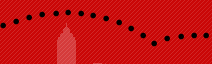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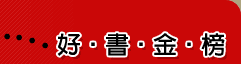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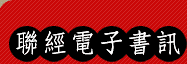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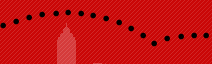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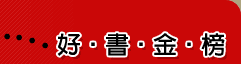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