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鬼之舞:第一幕 召喚
序章 炫目燈光下,克蘿伊的影子在舞台上拉得好長好長。她的腳趾往前繃緊,雙臂如翅膀揮舞,頸子往後弓,看著自己的剪影彷彿脫離控制,自行移動…… 一滴汗珠沿著胸線往下滑,被薄薄的緊身舞衣吸收。沒有音樂,舞台以外的空間是一片空蕩蕩的黑暗,然而她感覺得到主人的注視。她揚起下巴,對上他的雙眼,努力忍住顫抖。她緩緩往空中伸出修長纖細的腿。 他的手杖往地板一敲。「再一次。」 克蘿伊抹抹額角。長達數小時的練習,一點一點的汗水和鮮血撒在各處地面,但她沒有放棄。隨著編舞指導的報數,她周圍的十三名芭蕾舞者輕快地迴旋進出,掀起雪白漩渦,她們的鞋子輕巧地拍打木板舞台。 「一、二、三、四。」 她的雙腳動得比腦袋還快,悄悄滑過舞台。她的頭往後仰,雙臂向燈光展開。 「加快速度!」他大喊,她舞向芭蕾舞者圍成的圓圈,跟上她們的腳步。「轉化妳的身體!妳的骨頭是中空的!妳的雙腿只是羽毛!」 克蘿伊迅速旋轉,背脊拱成新月形,舞者掠過她身旁,她們臉上毫無表情,高速移動的腿腳像是帶著殘影。 「沒錯!」編舞指導勾起得意張狂的笑容。「沒錯!」 克蘿伊腦袋發暈,精疲力盡,舞衣被汗水濡溼,但她顧不了那麼多。長久以來的訓練終於奏效,不需多費力氣,她的雙腿優雅地相互交織,身體也流暢地跟上,像是溜過舞台的一匹絲緞。 放開自我,狂喜令她的頭後仰,胸口不斷起伏,濃稠高溫的空氣填滿肺葉。 那十三名舞者湊向她,她們的臉龐是蒼白的漩渦。克蘿伊彎腰閃過她們的撫觸,壓低身子,指尖擦過木頭地板,摸到奇異的熱度。淡淡的煙味在身旁翻捲,搔刮鼻腔,編舞指導的聲音離她好遠,帶著點水聲。頭上的燈光閃爍不定,往牆面投下詭異的影子。 一股熱浪傳遍她的身軀。那是無法辨識的奇異感知——熱燙的物體湧入血管,讓她的腦袋一抽一抽。 細如絲線的低語在她腦海泛開,太過輕細,難以理解。她甩甩頭,想要抖掉它們的糾纏,但它們相互融合,陌生、無法解讀,而且越來越響亮,越來越淒厲。 她雙眼灼熱。火紅在屋內巡行。硬鞋的緞帶緊緊纏住腳踝。她的雙腿無預警地往後彎曲,渾若無骨。她的手臂吱嘎作響,盪至頭頂。她的下巴不聽使喚,往上揚起,對上那一盞盞舞台燈。 我的,一道聲音在她腦中說著。 克蘿伊腳步踉蹌,雙腿顫抖努力維持平衡。她鼓起所有力氣,強迫嘴唇移動。「不!」她痙攣似地尖叫,體態崩毀。 舞者的雙腳僵在原處,臉龐茫然扭曲。編舞指導的聲音從黑暗中破空而來:「親愛的,這可是致命的錯誤。」 「什麼?」克蘿伊低喃:「怎麼會——」但字句被窒悶的熱氣淹沒。那股熱氣包覆著她,舔舐她的腿,她痛苦地扭轉身軀,那個形體控制住她,隨著一陣陣鼓動,從她的手指、手臂、胸口溢出,令她血液沸騰,直到無法忍受的灼熱狂喜填滿她。 她身周的色澤越來越清晰,明亮到眼珠也被燙熟。有個東西不斷搔刮耳膜——她這才發現那道震耳欲聾的尖吼是自己的聲音。 她化作耀眼的光芒,肉體融為灰燼。 第一章
母親唰地拉開窗簾,讓午後陽光流入房�。 凡娜莎擋住雙眼。「媽,拜託。」 「曬點太陽不會怎樣。」艾德勒太太後退一步,嘟著嘴打量屋內。「而且啊,陽光可以消毒。天知道這�有沒有好好打掃過。」她從皮包�挖出一小瓶乾洗手,往掌心擠了一大團。「細菌,給我滾!」 凡娜莎忍不住笑了出來,視線飄向四周。 這是間簡單的宿舍,設備陽春,只有兩張床、兩張書桌、兩張梳妝台。牆面漆成淡黃,釘在櫃門後的穿衣鏡中映出散在地上、尚未拆封的紙箱。房間的另一半已妝點上惹眼鮮艷的色彩:電影海報、拼布枕套、從櫃�湧出的大量衣服鞋子,可是凡娜莎的室友不知去向。 敞開的房門外,走廊上滿是輕快的說話聲——女孩們笑著閒聊暑假過得如何,家長邊抱怨邊扛著沉重的行李擠過走道,學生家中年幼的妹妹像發瘋的芭蕾舞者般原地轉圈。 凡娜莎曾經也是那些小女孩。可惜她幾乎記不得上回跳舞跳到笑出來的時刻。她吹開垂在頰上的一縷紅髮,瞥了父親一眼,但他只同情似地聳聳肩。 「這樣不太好。」母親將小花瓶從床邊小几一側移到另一側。「好多了。」不過在凡娜莎眼中,其實根本沒兩樣。 父親嘆了口氣,在他妻子看不到的角度向凡娜莎翻翻白眼。她笑出聲來。 「有什麼好笑?」母親的口氣嚴厲。 凡娜莎咬住嘴唇。「只是稍微想到以前的事。」 「別管以前發生什麼事。」母親的嗓音中帶著細微的顫動。「專注在當下。」她揉揉羽絨被的邊緣,一手撫過額頭,彷彿想抹去過去數年來被壓力和憂慮烙下的深刻線條。「當然了,待在這�沒什麼好處。」 有人敲門。紮著高馬尾的女孩站在走廊上,抱著一塊寫字板。 「有什麼事嗎?」凡娜莎的母親應道,她看看從女孩短褲下緣延伸出的健美雙腿。 「嗨。我來找凡娜莎•艾德勒。」 凡娜莎往門邊踏出一步,但她母親不為所動。 「我是她母親艾德勒太太。妳是?」 「喔,我是住宿生顧問凱特。」女孩偷瞄房內景況。「我來歡迎凡娜莎加入紐約芭蕾學院。」 「住宿生顧問?只有妳一個?」 「其實有兩個。」凱特開心地說明。她有雙明亮的藍眼,淺棕色髮絲間帶著些許金光。「我負責一年級女生,班負責男孩那邊。」 艾德勒太太皺眉。「我可能誤會了。妳的意思是就妳一個人負責所有一年級女生?」 凡娜莎掃瑟縮一下,凱特諒解地看了她一眼,對艾德勒太太露出可靠的笑容。「是的。但我可以保證——」 艾德勒太太打斷她。「妳知道紐約芭蕾學院每年只錄取二十個跟凡娜莎同年的舞者嗎?」 「我知道——」 「十五歲可是很敏感的年紀。」 凡娜莎的臉開始發熱。 「我知道。不久前我也是十五歲——」凱特又說。 「就是這樣!」艾德勒太太舉起雙手。「妳不比凡娜莎大多少。妳怎麼能掌握她的行蹤、她跟誰在一起?她寫作業、練舞的時候,外頭可是有千百個讓她分心的誘惑!曼哈頓到處都是獵捕天真女孩的野獸。」 寢室內外的人似乎都倒抽一口氣,包括一把抓住梳妝台的艾德勒太太,她揮手對頸子搧風。此時此刻,凡娜莎真希望父親介入,對母親說她太超過了——但她爸媽的相處模式並非如此。一向是由母親負責下令;爸爸只是乖乖聽話。 「抱歉。」她母親恢復冷靜。「我只是擔心她。」她轉頭對凡娜莎說:「我知道妳很想跳舞。我真的知道;我以前也是這樣。但妳真的確定想待在這�?這地方還有其他東西,整個世界——」 「媽,我不會有事。別擔心我。」 她們已經談過這件事——非常多次。母親希望她待在康乃狄克州念公立學校。但凡娜莎想的是……嗯,這跟她想怎麼做無關。重點在於她得做什麼。 那就是待在這�。待在紐約芭蕾學院。這是瑪格莉特曾經讀過的學校。 收到錄取通知信後,她抗爭了好幾個月才說服母親點頭。凡娜莎獲得全額獎學金,這點或許也幫了點忙。「她是我們面試過最有天分的舞者。」招生部門的行政人員說:「這份天賦一定是家族遺傳。」 艾德勒太太終於屈服。 凡娜莎向凱特愧疚地聳聳肩,希望自己的名聲沒被母親的怒罵摧毀。在只有二十名學生、男女各半的班級�,被人排擠可不是她嚮往的嶄新開始。不過凱特的反應出乎凡娜莎意料,她眨眨眼,轉向艾德勒太太。 「曼哈頓確實是個充滿刺激的地方。」街上吵雜的喇叭聲加重了她這番話的分量。「我無法向妳承諾能完全掌握凡娜莎的行蹤,但我敢說我們盡了一切努力,讓所有學生安全又快樂。這�有嚴格的門禁,況且每個人都忙到幾乎沒空體驗這座城市。」 艾德勒太太軟化了些。「好吧。」 「很好。」凱特把寫字板夾在腋下。「就不打擾你們整理了。凡娜莎,兩小時後有場新生輔導活動,地點是茱莉亞音樂學院的三樓大教室,到時我們會再見面。如果妳還有其它問題,我就在這附近走動。」 艾德勒太太瞄了凡娜莎一眼,接著踏出門外。「我是有幾個問題要問。」說著,她跟凱特走遠。 等到兩人聽不見房內的聲音,凡娜莎搖散蓬亂的紅髮。「根本就是神經病。」 她父親笑了笑,抹去額頭的汗水。他的面容俊朗,凡娜莎遺傳到他分明的出色五官,還有身高,以及如火的頭髮,只是他的紅髮已經轉成好看的紅褐色。她跟母親或姊姊瑪格莉特不同,不是嬌嫩的花朵,她之所以能成為令人屏息的舞者,或許這是部分原因。沒人想得到她能擺脫重力,但她的大跳(grand jeté)彷彿在空中飄浮,輕巧得像一陣風;腳尖劃過舞台,她化作白天鵝、睡美人、糖梅仙子,那頭紅髮在燈光下閃耀,宛如一道電流。 他捲起袖子,從她的梳妝台上拿起一雙芭蕾舞鞋,緞帶從指間滑落。那雙舞鞋在他掌心顯得好小好小。「娜娜,妳知道,如果在這�不快樂的話,可以告訴我。」 一群女孩走過房門外,語笑嫣然。凡娜莎咬住下唇,希望自己想待在這�的心意跟她們一樣強烈。紐約芭蕾學院是全國頂尖的舞蹈學校,她應該要想待在這�,但她的心從未在此停留,至少到最近都是如此。深愛芭蕾舞的是她姊姊,在夢中細數舞步、幻想登台的人是瑪格莉特。凡娜莎只是跟著她的步伐。 可是呢,不知道為何,中學的她發現自己跟練舞用的扶手相處的時間超過她的朋友。她心中有個角落只想念公立高中,跟朋友一起吃起司漢堡而沒有任何罪惡感,然後跟某個沒有緊身褲或彈性舞衣的男生約會。那時她以為這是做得到的,可是這份想望隨著瑪格莉特一同崩毀。 凡娜莎嘆口氣。「你知道我走不了。」她望向門口。「我知道她很難受,可是失去家人的不只她一個。」 「她怕妳受傷。她不喜歡這�。」父親小心翼翼把舞鞋放回梳妝台上。 「爸,別擔心。這�不過是所學校。」 「我知道。可是妳媽,她相信……嗯,妳也知道她怎麼想。她寧可妳去讀任何一所其他學校。如果妳覺得這是最好的選擇,那我會支持妳。但要是壓力大到無法負荷,妳隨時都可以回家,選擇不同的道路。」 爸爸勾起一邊嘴角,拍拍凡娜莎的肩膀。她懂他的意思,可是不同的道路在哪?她外婆曾是首席舞者,她母親曾是首席舞者,瑪格莉特曾是這所學校最有前途的學生之一。 直到她三年前失蹤為止。 凡娜莎還記得他們接到電話的那一刻。那年二月,麻州已降下白雪,朵朵雪花飄過家中廚房窗外,她跟爸媽正共進晚餐。她姊姊跑出校外,課程顧問對她母親說:「她跟不正派的人來往。」又說:「練舞的壓力有時會讓這些女孩走上歧途,無論我們盡了多大努力都無法阻止她們。」 當晚,爸媽把凡娜莎送去祖父母家,開車前往紐約找瑪格莉特。他們白天跟警方合作,晚上則在城�各處搜索,踏遍最黑暗、最荒涼的角落。過了兩、三個星期,父親回麻州繼續工作,週末到紐約與妻子會合。 六個月後,爸媽放棄搜索,回家照顧他們僅剩的小女兒。原本屬於瑪格莉特的雜物也運回來,收在車庫�。 凡娜莎很想相信瑪格莉特還活在某個地方,跟朋友一同歡笑,跟普通少女一般過著夢幻人生。 他們從紐約芭蕾學院收到最後一件包裹:瑪格莉特的學生證、一件還帶著她身上微微花香的舞衣、一雙破舊的硬鞋,這些都是他們從她的練舞教室置物櫃清出的東西。一打開盒子,凡娜莎的母親馬上哭了出來,她看到舞鞋鞋底刻著瑪格莉特的姓名縮寫,瑪格莉特一直留著那雙舊鞋,因為那是她在麻州的舞蹈老師送的禮物。「她是不是死了?」母親輕聲說出縈繞在全家人心中的想法。 凡娜莎坐下,頭靠上母親的肩膀。「說不定她只是再也不需要這些東西了。」她拒絕相信姊姊已不在人世。 之後,凡娜莎跟父親努力恢復原本的生活,母親卻幾乎一個月下不了床。她不再沖澡更衣,什麼都不吃,甚至拒聽古典音樂。這時凡娜莎知道事態不對。 因此,在某個沉鬱的星期五,她從衣櫃偷偷拿出自己的舞鞋,踮腳走進主臥室,她母親正蜷在被子下一動不動。雨水沿著窗玻璃滑下,凡娜莎跳起舞,讓所有悲痛從心中傾瀉而出,直到她只感覺到赤裸裸的心跳。 母親緩緩坐起。 不久,她恢復原本的習慣,開車送凡娜莎去上芭蕾課,直到某天凡娜莎宣佈她要申請紐約芭蕾學院。母親嚇呆了。她很喜歡看凡娜莎跳舞,卻從未想到凡娜莎熱愛舞蹈的程度竟會讓她跟隨瑪格莉特的腳步。他們已經封閉了那條人生的道路,她說。 可是凡娜莎沒有屈服。藉由父親的協助,她申請了瑪格莉特消失無蹤的那所學校,因為她不只下定決心要跳舞,還要找到姊姊。她得待在這�——待在這所學校,待在曾經屬於母親跟瑪格莉特的命運中。 現在她父親拉開一個紙箱,坐在凡娜莎身邊。「我是認真的。」他說:「我知道妳是很有天分的舞者。我只想確定妳也能快樂。」 「我很快樂啊。」凡娜莎應道。大概吧,她在心中暗忖。快樂總是如此複雜。 「誰很快樂?」母親的提問把父女倆嚇了一跳,她悄悄進門,拿亞麻手帕擦拭眼角。她總是這樣悄悄靠近,在凡娜莎的生命中無孔不入。 「是我。」凡娜莎擠出微笑。「我很高興能來這�。」 「當然囉。」母親語氣傷感。「這是全世界最頂尖的芭蕾舞學校。」她生硬的笑容掩不住臉上憂慮的線條。「我剛才去看了瑪格莉特以前的寢室。」她嗓音沙啞,凡娜莎的父親一手環上她的肩膀。「答應我,妳絕對不會吃任何藥。連阿斯匹靈都不准吃。我才不管妳腳有多痛。」 「別擔心。」凡娜莎知道其他女孩會吃止痛藥,不過她長滿厚繭的腳掌已經麻木到極點,就算用指甲猛戳大概也不會有感覺。 再過一下,把最後幾個空箱清掉,她父親緊緊抱住她好一會兒。「有什麼需要就打電話給我。任何事都可以。」他輕聲說:「就算聊天也好。」 父親語氣中的柔情出乎她的意料,凡娜莎在他懷抱中放鬆。吸入他身上鬚後水的氣味,她察覺到今天到此為止,儘管他們花了一天整理行李,但現在她才意識到自己不會跟他們回家了。凡娜莎臉頰緊貼他的衣領。「我會的。」 「好啦。」母親說:「輪到我了。」凡娜莎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她一把拉進懷�,用力抱住,她的臉埋入凡娜莎的髮中。「喔,我一定會很想妳。」母親抱著她,輕輕搖晃。「妳一定會變得很厲害。我知道妳一定做得到。」 凡娜莎雙手環上母親纖細的身軀。「媽,謝謝。」
突然間,母親像是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事似地鬆開她,往後退開,撫平裙面縐褶,拿面紙擦擦眼角。「我們該走了。」她說得乾脆。 凡娜莎看著雙親消失在走廊末端。現在該怎麼辦?她拎起放在床上的小盒子,�頭放著瑪格莉特的硬鞋,緞帶纏繞著破舊的粉紅緞布鞋面。她輕輕撫過刻在鞋底名字縮寫的粗糙線條。她才剛把那雙硬鞋塞進櫃子,一個女孩就衝進寢室。 「那是妳媽?那個門都沒敲就闖進我房間的瘋婆子?還一直提到什麼瑪格莉特?」她又高又瘦,膚色深褐,擁有一雙銳利的綠色眼眸,臉上帶著一抹笑意。 「抱歉。」凡娜莎縮了一下。「她這幾年都是這樣對我,希望這會讓妳好過一點。」 「媽呀,我以為我媽已經很惡劣了。」 凡娜莎咬咬嘴唇。「她沒碰妳的東西吧?」 女孩濃密的頭髮用大髮夾往後固定。「沒有,她只是站在房�,好像在發抖。我以為她要坐到我床上,可是我在她行動前開口提醒了她。我可能把她惹哭了。」 「不是妳的錯。」凡娜莎搖搖頭。「她最近很常哭。」她頓了一下。「對了,我是凡娜莎。」 「凡娜莎?那誰是瑪格莉特?」 「我姊姊。她以前在這�學舞……可是現在她不在這�。」 「真感人的故事。」女孩雙眼發亮。「我是史黛菲。」 另一個女孩探頭進房。「我叫TJ。」她咧嘴一笑。「妳的室友。」 她頂著一雙母鹿似的大眼和滿臉雀斑,糾結的棕色捲髮夾在頭頂,幾縷鬈髮在臉頰周圍跳躍。「是譚美•潔西卡(Tammy Jessica)的縮寫,不過我覺得這名字太娘了。妳不覺得TJ好聽多了嗎?」 凡娜莎點頭。「大概吧。」 「請定義何謂『好聽』。」史黛菲說。 「很高興認識妳。」TJ坐在她的亮藍色床單上。從舞者的角度來看,她的骨架有點大。「都進了這學校,我要來創新一下。TJ的T可以代表跟指甲一樣堅硬(tough)。J就代表爵士樂(jazz)囉。隨便啦。反正現在我就是TJ。我要不斷前進。」 凡娜莎笑了。新的開始聽起來很棒。TJ這名字跟她的外表很搭:她沒化妝,連眼線都沒上。她的表情就夠生動了。 「我是城�人。」TJ的語氣像是全世界只有紐約算得上城市。「上東城。其實我可以住家�,可是我想擺脫爸媽。他們是律師,合開了普利勒事務所,我家就是那種調調,他們總在講話、講話、講話。」她翻個白眼。「可以離開那種環境真是太好了。」 凡娜莎努力忍笑。講話、講話、講話。「普利勒?」她說:「是紐約芭蕾學院董事的那個普利勒嗎?」 史黛菲轉頭問:「TJ,妳沒跟我說這件事耶。」 TJ沉默一會兒。「幹嘛說出來?這跟我被錄取又沒關係。」 「當然沒有。」史黛菲說。 「我沒那意思——」 可是凡娜莎的解釋被TJ打斷,她打個哈哈。「我知道。妳從哪來的?等等,先讓我猜猜。加州。不對,是佛蒙特吧。」 「很接近了。是麻州。」 TJ發現凡娜莎偷瞄她床上那堆衣服,她說:「別擔心,我可不是一直這麼邋遢。」 凡娜莎笑出聲來。「我也是。」 「別再提妳那堆衣服啦。」史黛菲說:「真不敢相信我們竟然可以在曼哈頓上學。不覺得很酷嗎?」 「這�可是不夜城呢。」TJ說。 「人行道上還鋪滿黃金!我是不是把這跟好萊塢搞混了?」 「沒差啦。」凡娜莎說:「重點是我們有夠幸運。」 「明天早上我一起床就要去時報廣場。」史黛菲推開TJ,啪地坐到凡娜莎床上。 「噁。」TJ說:「明天早上我絕對不會去時報廣場。」 「時報廣場怎麼了嗎?」史黛菲問。 「對觀光客來說沒什麼問題。」 「喔,我就是觀光客啊。我又不是那種在這�住了一輩子的老太婆。」 三個女孩望向窗外,林肯中心被暮色籠罩,熠熠生輝。中央廣場的噴泉將水柱高高噴起,凡娜莎已經把四周的幾幢雄偉建築牢記在心:擁有華貴玻璃大門的是紐約市芭蕾舞團;高聳的拱形窗屬於大都會歌劇院;黃色大理石建築是艾佛利.費雪廳,紐約愛樂的地盤。她們的新學校紐約芭蕾學院座落於艾佛利.費雪廳後頭,隔壁則是茱莉亞音樂學院。這兩幢平凡無奇的建築現在成了凡娜莎的家園。落日餘暉將三人眼前的一切全都染成黃銅色——從噴泉到屋舍到廣場;從許多公寓頂樓圍上木板的閃耀水塔,到遠處窗戶猶如融金的摩天大樓。 「真是太美了。」史黛菲語氣中的鋒芒一瞬間消失。「真不敢相信我們要在這�待上四年。感覺我們就在宇宙的中心。」 「差不多啦。」TJ說:「紐約市還有很多我們這輩子大概不會見識到的地方。林肯中心就像個安全的小泡泡。」 也沒安全到哪去,凡娜莎心�這麼想,但說出口的卻是「感覺不像真的,對吧?感覺明天我會在家�醒來,發現這只是一場夢。」 「等開始上課就知道了。」TJ笑了笑,露出一口閃亮的白牙。「等到我們的腳起水泡跟流血後,妳就知道有多真實了。」 凡娜莎的腳趾反射似地在帆布鞋�蜷曲。她忍不住望向史黛菲結實的大腿、TJ筆直的背脊,心想她們會不會是比她更優秀的舞者。她還不習慣被這麼多認真學舞的同儕包圍;在家鄉,凡娜莎的表現總是遠遠超越眾人。 她的思緒被另外兩個鑽進寢室的同學打斷:其中一人是嬌小的艾莉,史黛菲的室友,她一頭金髮,一手挾著筆電,跟在背後的是個亞洲男孩。 「我們聽到這�有人在說話,想來打個招呼。」男孩說:「因為我們都超厲害,妳們一定會想認識我們。我叫布藍。」他對著空氣伸手,彷彿在等哪個人親吻他的手背。 史黛菲扮個鬼臉,坐到窗台上,蹺起深褐色的長腿,上下打量剛上門的訪客。 「那不是他的本名。」艾莉逗弄似地說,甜美的嗓音帶著南方口音。她的五官樣貌都像裹上糖衣,讓人能夠一口咬下:黃色的鮑伯頭、圓圓的鼻子、微噘的嘴唇。就連衣服都是帶著蕾絲的嫩粉紅色。她用手肘推推布藍。「說啊,快講!」 布藍搖搖頭,有些認真地瞥了她一眼。「妳敢就試試看。」 TJ撥開頸子前的髮絲。「所以說你本名叫什麼?」 布藍正面迎擊:「我絕對不會說。」 「為什麼?」TJ看了看布藍和艾莉。「你不是已經跟她說了?」 「因為我們都是從南方來的。她知道。」 「知道什麼?」史黛菲問。 「那�的人都很怪。」布藍的語氣像在說明顯而易見的事實。 「身材也很寬。」TJ替他補充。 布藍聳聳肩。「沒錯。跟妳們說,我是日本跟墨西哥混血,有多少人會拿瑪格莉特配清酒?」 「清酒是什麼?」TJ輕聲問凡娜莎。 「再加上我又是個喜歡穿緊身褲跟舞鞋的男孩。」布藍繼續說:「還不吃紅肉。在德州長大可不輕鬆。你們知道在那�要找到一份還可以的沙拉有多難嗎?」 房�頓時充滿女孩的咯咯笑聲。「沒那麼慘啦。」艾莉坐到TJ旁邊。「而且南方確實有個其他地方沒有的特色。」 「過量的山露汽水(Mountain Dew)?」TJ開了個玩笑。 艾莉勾起嘴角,粉紅色唇瓣彎成新月形。「南方紳士,特別是從阿拉巴馬州來的。」 布藍翻翻白眼。「在我眼中他們都是農夫,手�還拿著超大鋤頭。」 凡娜莎笑出聲。「我喜歡看人穿襯衫加工作服搭西裝外套跟小領結。」她說:「不過我是麻州人。我喜歡中學男生。」 「看,我說得沒錯吧。」布藍說:「要不然我也可以勉強拿俄羅斯芭蕾舞者來充數。我愛他們嚴謹的個性。就算不說英文也沒關係。只要他可以一邊在床上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一邊拿魚子醬餵我就好,然後還要陪我玩俄羅斯娃娃。」他頓了一下。「可是我沒有俄羅斯娃娃。」凡娜莎跟其他女孩繼續盯著他看。 「那你們怎麼溝通。」艾莉滿腹疑竇。 「親愛的。」布藍傾身向前,睫毛上下舞動。「愛情的語言不需要字句。妳沒看過『小美人魚』嗎?」 連史黛菲都笑了。「別再提俄羅斯男人、玩偶跟迪士尼電影啦。我們是來這�跳舞的。」 艾莉打開粉紅色外殼的筆電,蓋子上還有顆斗大的心形,讓他們看看曾經從這所學校畢業的知名舞者照片:在《吉賽兒》劇中擔任女主角的安娜史塔西亞•佩多娃、扮演《胡桃鉗》中結實的鼠王的亞歷山大•葛瑞爾、茱莉安娜•法拉多把《睡美人》�頭的歐蘿菈公主詮釋得飄逸輕靈。 「他們是成功的舞者。」布藍說:「那麼,失敗的舞者呢?」 凡娜莎渾身僵硬。「這什麼意思?」 艾莉插話:「聽說去年有個女孩練習時摔斷腿。其中一個男舞者害她從空中摔下來。某個學長跟我說他還聽到骨頭斷掉的聲音。」 凡娜莎縮了一下。 「入學時是二十個人。」TJ吟詠似地說:「可是沒多少人能撐到畢業。」 「我是認真的。」布藍說:「總會有學生受傷。」 「更別說摔斷腳趾了。」史黛菲附和。「我去年差點中招。」她扭扭腳踝,銀色的細踝鏈發出細碎聲響。 「或是破碎的心。」艾莉羞赧地看了布藍一眼。他拿起枕頭丟向她。 「或是因為體重或藥物問題被送回家的女孩。」凡娜莎補充。 「你們跳舞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史黛菲話鋒一轉。「就像——」 「失去理智?」凡娜莎被自己脫口而出的話嚇了一跳。 「呃——不是啦,我想說的是輕飄飄的感覺。」 「失去理智?」TJ臉上帶著興致勃勃的笑容。「妳是說頭暈目眩?可能是因為沒對好焦點吧。」 凡娜莎膽怯地笑了一聲。「開玩笑而已。」她覺得好尷尬。 那種感覺只是偶爾發生——失去神智的奇異感覺。當凡娜莎跳出最完美的舞步,音樂就像她心跳的一部分,周圍的世界開始旋轉,化為虛無,她彷彿失去自我。或許只是脫水症狀吧。每回她提起這件事,母親總是如此解釋。 凡娜莎抬起頭,發現史黛菲正在打量她。她臉一熱,但史黛菲包容地對她微笑,像在對她說:不管什麼祕密都可以告訴我。 「新生輔導!」艾莉突然大叫,打斷布藍的話頭。寢室外的走廊出奇安靜。「天啊,我們已經遲到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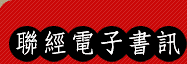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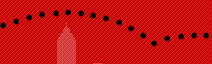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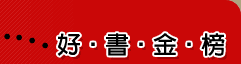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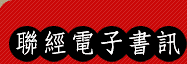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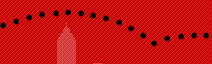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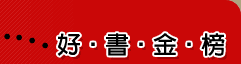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