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
一部有關近代中國男性心態史的專著
以明清以來的笑話書、俗曲、豔情小說
與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等史料
探究明末至民初之間男性的情緒、欲望、身體與私人生活
並分析其所反映之思想、文化意涵。
※ ※ ※ 導論(節錄)
一場男性心靈的狂歡節/黃克武 小說以勸懲為主,然非風流跌蕩,不能悅觀者之目,非謔浪詼諧,不能解聽者之頤。此書一出,天下無愁人矣。(《肉蒲團》扉頁題辭) 近年來受到性別(gender)觀念的影響,性別史成為中國歷史研究中一個新興的領域,然而多數中國性別史的作品集中於女性史(或稱婦女史),只有少數人關注男性史(history of man as man)、男同志或男性氣概(masculinity)的研究,或者承認「男性史」與「女性史」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書是以歷史與文學材料來探究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之間,男性的情緒、慾望、身體與私人生活,分為諧謔、情慾與現代轉型等三篇。書中處理的素材主要為明清以來的笑話書、俗曲、小說(主要是豔情小說,或稱為色情小說、性小說、性愛小說)與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等,而關懷的焦點是近代中國在傳統至現代的轉換中,男性世界中幽默感、情慾表達與身體觀念之間的關係。這三者構成了男性生活與思想的重要面向,而聚焦於《金瓶梅》中所謂「言不褻不笑」,亦即以有關身體、情慾相關的「猥褻」話題作為談笑之資。 上述這些文本雖不乏女性讀者,且部分文本亦描寫女子之情緒、感受,又涉及男女之互動,然筆者認為明清諧謔書刊與豔情小說主要反映了男性中心的社會中,男性菁英分子所塑造出來的對身體、情慾與兩性關係的看法。這些看法一方面狂野大膽、繽紛多彩,以「謔浪詼諧」之手筆書寫情慾活動與身體感受,另一方面則與儒家倫理、道家養生與佛教果報等理念交織在一起,企圖醒世覺民。清末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主要處理身體與情慾面,與人們對性的困擾,而較不談諧謔。這些醫藥廣告反映在二十世紀初年之後,傳統的身體觀、情慾觀在西方現代醫學、國族主義、跨國公司全球市場、新興媒體的衝擊之下所發生的變化。直至今日這些文本仍廣泛地流傳於中文世界,而其中所反映出來的「縈繞於心的性幻想與性恐懼」以及「言不褻不笑」等心態亦仍普遍地存在,構成中國文化圈中男性對於性別認知(尤其是對「男性氣概」的界定)、情慾表述與隱私觀念的重要基礎。最後一章則處理近代中國私領域與隱私觀念的出現,及其所造成的影響。 本書各章及附錄的幾篇短文,構思與寫作的時間從一九八○年代後期開始,迄今近三十年。在寫作之時我並不意識到我處理的課題與男性史之間的關聯,而主要受到學界中「文化轉向」、「新文化史」等趨勢的影響。二○一四年我開始將這些文章整合成一本專書時,才逐漸領悟到我所寫的其實不是普遍的「歷史」(History),而只是「他的故事」(his story)。這是性別意識對我治史觀念的一大衝擊。 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看,本書所分析的幾類文本:豔情小說、俗曲、笑話書與醫藥廣告等可謂一場男性心靈上的「狂歡節」,可稱之為「狂歡節話語」。「狂歡節話語」(“Carnivalesque” discourse)是一個源於俄國學者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觀念,意指以幽默、混亂來顛覆主流論述的一種文本模式(literary mode)。在西方世界狂歡節(亦稱「嘉年華會」)期間,傳統的日常生活、社會規約與階級劃分都被打破,簡單地說是將傳統秩序徹底翻轉,並對所有習以為常的觀念加以抨擊。根據巴赫汀所述,「狂歡節話語」把「肉體的低下部位」和「肉體的物質性原則」提得很高,「是對肉體感性慾望的正面肯定和讚美」;「將一元統一的官方語言所掩蓋和壓制的眾聲喧譁現象昭然於眾」,並「讓溫文爾雅、矯揉造作的官方和菁英文化尷尬」,因而展現了大眾文化的革命性格。「狂歡節話語」和巴赫汀「醜怪」(grotesque)的觀念有密切的關係。「醜怪」是一種相對於官方主流文化的一種狀態。官方文化強調的是一種嚴肅、完整、永恆、秩序、一致,和循規蹈矩的生活與理念,「醜怪」則企圖解除這類規約,是一種對國家或教會權力的僭越、質疑、抗拒和解構。它使身體和生活能在大吃大喝、大笑大鬧中獲得紓解與再創造,並使社會獲得一種新的活力。如果借用巴赫汀的觀念,本文所分析的明清以來中國的笑話書刊、豔情小說與醫藥廣告等,一方面具有諧謔、逗趣之性質,另一方面則公開述說身體、情慾之私密感受,並對禮教加以嘲諷(可謂「白晝宣淫」),都可以屬於具有「醜怪」性質的「狂歡節話語」。我們也可以將此類文本比擬為一場「社會的夢」,其內容部分為男性集體心態之展現。這些文本中的內容是以折射、扭曲、誇大的方式表達出受到禮教與法律所壓抑的各種慾望,因而具有「反社會性」。難怪有學者認為晚明俗文學興起的精神背景是出於一種「真」的追求,表現出一種「自由的精神面貌,沒有任何道統規範,可以隨心所欲地戀愛,或表現慾望的純潔無垢」。不過我們也不宜過度強調近代中國「狂歡節話語」的批判性與革命性,這些文本的創造者(與讀者)主要為男性菁英階層,而且他們一方面固然以大膽的諧謔想像挑戰了既有的社會規範,但另一方面,這些光怪陸離、驚世駭俗的挑戰並非全然背離現有秩序,反而有一部分是維護既有的男性中心的體制,造成情慾與禮教、私情與公義之間的拉扯與較勁。 這種近代中國男性「狂歡節話語」中既革命、又保守的性格,以及人類情緒、感受的歷史與文化面向,是本書關懷的重點。傳統歷史學比較重視人類生活中公共面與理智面,而不處理私人生活中的情緒與身體等課題。這一部分是因為許多人認為這兩個領域都受生理影響,有較強的普遍性,因而可由科學來研究,或文學與藝術來反映。然而,隨著法國年鑑學派對「心態史」之提倡、人類學中「文化」觀念對歷史學的衝擊,以及史學界所發生的「文化轉向」等,性別史、情緒史與身體史逐漸變成歷史研究之課題,並儼然躍升為非常熱門的研究題目。 筆者對文化史的興趣源於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筆者在東海大學參與高承恕、林載爵、蔡英文等先生主持的「科際整合討論會」(一九七九─一九八三),該會之參與者有社會、政治、經濟與歷史系的老師與學生。當時高承恕教授帶著學術研究本土化的夢想,遵循「不離事而言理」的古訓,帶領大家「一頭跳進歷史之中」。讀書會的成員開始從英法歷史的比較來思索「西方之所以成為今日之西方」。接著又從歷史與社會之接榫點走向年鑑學派的作品。在這期間,討論會中大家不但閱讀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與其他有關西方歷史文化的書,一起吃喝談笑,也因為翟本瑞、陳介玄的關係,我接觸到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與布紐爾(Luis Buñuel, 1900-1983)的超寫實主義電影。其中布紐爾的《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 1967)、《布爾喬亞拘謹的風采》(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 1972)、《自由的幻影》(The Phantom of Liberty , 1974))等片讓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電影的共同主題即是慾望、道德、諧謔、嘲諷等心靈現象。對布紐爾來說,性的本身並不獨立存在,它一方依賴道德與罪惡感而生,另一方面,在慾望舒展的心理過程之中,真實與虛幻很難區別。 然而這些西方作品所展現的心靈世界與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狀況有何異同?我們應如何借用西方經驗的靈感來反思中國?好友翟本瑞也因此開始研究動物分類、笑話書、春宮畫等。在這些想法的激勵之下,在我心中浮現的不但是「西方之所以成為今日之西方」,也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之中國」。 一九八八年我赴英國牛津大學讀書,指導老師是專門研究道教與戲曲史的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教授,以及研究中國近世經濟史、文化史的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龍教授為我奠定漢學研究的基礎,也讓我一窺中國庶民生活中的戲曲、宗教世界。伊懋可教授對我的影響更大,那時他正在撰寫 Changing Sto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一書稿。該書研究十九世紀初葉以來的一些文本,如李汝珍的《鏡花緣》、張應昌編輯的《清詩鐸》、網珠生的小說《人海潮》、浩然的小說《西沙兒女》、司馬中原的小說《孽種》等,處理中國在不同時期的價值與情感,及其所映現的歷史世界。在他的鼓勵下,我開始研究《鏡花緣》的幽默。同時,伊懋可教授介紹我閱讀當時同樣在牛津大學教書的法國史家 Theodore Zeldin 教授有關法國情緒史的作品,以及當時劍橋大學出版社剛出版的一本法國中古以來清潔觀念的歷史著作。Theodore Zeldin 的書處理一八四八─一九四五年間的野心、愛情、憤怒、驕傲、品味與焦慮等課題。Georges Vigarello 的 Concepts of Cleanliness: Changing Attitudes in France since the Middle Ages 則研究過去一千年來法國人對清潔、健康與衛生的看法。這兩本書都對我有所啟發。一九九四年我返回台灣,從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我參加了由熊秉真教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社會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又主持了國科會計畫「明清豔情小說的文化史分析」(由李心怡、黃夙慧等人擔任助理)。在這些計畫之中我的研究主題以「幽默史」為中心,拓展到與幽默相關的身體與情慾等課題,本書的多篇文章是上述主題計畫與國科會計畫的產物。這些文章的完成也得力於一九九五年陳慶浩與王秋桂所編輯的《思無邪匯寶》的出版,這一套書廣泛蒐羅了全世界各圖書館所藏豔情小說之善本,為此一研究奠定重要的文本基礎。 我的核心問題是「幽默感」與「身體感」所交織而成的明清以降中國男性的心態史,亦即男性談笑之內容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而不同時期之笑話、小說如何表現出人們身體感、情慾觀?眾所周知,笑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也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現象,長久以來笑話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例如佛洛依德、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有關笑話理論的研究,探究為何笑話可笑,以及其背後之心理與語言機制。至於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哲學的研究視角,則探討幽默的社會、政治、思想功能與運作。例如,人類學者強調:笑話與文化背景之關聯;政治學者與社會學者則處理族群笑話(愛爾蘭人、波蘭人、蘇北人)、政治卡通、幽默與人際溝通(例如注意以幽默化解人際之緊張的社會功能);哲學家探究幽默與哲思之關聯(如禪宗的話頭如何啟發智慧)等。文學領域(尤其通俗文學)之中,笑話研究為一重要課題,例如在西方有不少學者研究莎士比亞的幽默。 在中國研究的範疇內,笑話主要是由文學研究者擔綱,如周作人、婁子匡、王利器、趙景深、黃慶聲、陳萬益、林淑貞等人作了大量的有關中國笑話史的研究。此一研究取向有階級性的假定,他們傾向於將笑話視為源於下層社會、口語傳統,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意雅俗、士庶之區別往往並不那麼明確。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明清諧謔世界中的身體與情慾 前言:情慾生活的私密與揭露 許多學者都指出,人類情慾生活的一項重要特色在於私密與揭露的弔詭性。在絕大多數哺乳類(甚至靈長類)動物中,性活動都是公開的,只有人類在文明演化過程之中將性隱藏起來。在此情境之下,與情慾相關的身體器官(特別是具有性徵的部位)或活動(如自慰或交歡),成為個人私密生活的核心部分,公開談論即被視為猥褻。然而,性的私密與隱藏卻往往引發他人窺探的慾望,而越是隱藏,就越增加窺探時所帶來的快感。這樣一來,性的隱藏成為維護「文明」尊嚴的必要措施;而性的揭露(如呈現裸體或情慾活動),無論是日常的言說、姿態,還是採取文學、藝術的表達,或「科學」的研究,對訊息的創造者與消費者來說,似乎都帶有某種程度以窺探來追求愉悅的色彩,而須承受道德壓力。
人類情慾生活的私密與揭露雖有較強的普遍性格,然在不同文化(或時代)之中,法律與禮教規範的寬嚴(如私人領域的範疇、性禁忌的尺度),以及身體與情慾世界的揭露方式,卻有很不相同的表現。例如在西方以文學、藝術方式來揭露性的議題有長遠的傳統。在科學方面,佛洛依德以性的揭露來建構心理分析的學術世界;金賽(Alfred Charles Kinsey, 1894-1956)則以性的研究建立「性學」,迫使人們面對規範與實際之間的矛盾,並對根深柢固的道德觀念做出挑戰。 在明清時代中國情慾世界的私密與揭露也展現出多采多姿的景象。以當時頗為流行的一些出版品,如笑話書、豔情小說與春宮畫等來說,貫穿這三類史料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性的揭露與幽默感之間的關聯性。換言之,情色諧謔的挑逗與觸探和人們潛藏的性意識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不少學者都同意「猥褻」的主題是引人發笑的一個利器。如同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所說「給我一個面具,我會告訴你真相」,在幽默面具的保護之下(因為搞笑是不算數的),人們大膽地觸及性的禁忌,滿足揭露與偷窺的快感;又如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四七)所述:性笑話與呵癢類似,「有一種無敵的刺激力,便去引起人生最強的大欲,促其進行,不過並未抵於實現而以一笑了事」,這樣的「笑」似乎有助於解除禮教給予人們沉重的負擔,這也是一些學者所謂黃色笑話具有「社會安全瓣」(a safety valve)的功能。然而情色諧謔的複雜性還不只於此,它與人們對性的恐懼、人我之間的階級、性別、職業與年齡區隔,和對現實的批判意識等糾結在一起,而此類批判可能是對現實秩序的抗議與反省,也可能是為了糾正放蕩行為,維護禮教(或特定人群)之權威。 本文所謂的「諧謔世界」是指人們以搞笑為目的所創造的精神世界,而為了探索此一精神世界的軌跡,筆者擬利用明清時期一些幽默性的文本來作整體的分析,而暫不討論文本與實踐之間的關聯性,也不討論此一時期內部較為細緻的變遷。因此拙文的著重點不在社會實踐,而主要嘗試從私密與揭露的弔詭關係,來探討明清時期諧謔文本中的情慾表達(representation)。筆者的出發點是:與情慾相關的諧謔是一種文化現象,它的表現方式、目的與形式都具時代特色。這也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所指出的:笑是一種社會行為,有其自身的符碼、儀式、演員、劇場與觀眾;以及 Mary Douglas 所謂幽默與社會結構的直接對應性,搞笑的產生是因為社會生活之中本來包含了矛盾、對抗與失諧,它們藉著幽默論述而得以表達出來。 在本文之中作者將利用幾種明清時期具有諧謔性質的笑話、豔情小說、筆記故事、歌謠等來探討以下的問題:諧謔文本以哪些方式、揭露出何種的情慾世界?此一情慾世界又蘊含了何種的「性意識」?再者,此一性意識與明清時期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與文化有何關聯?本文所徵引的一部分明清史料從官方的角度來看,乃是「淫書」、「淫曲」與「淫詞」,這些文本因為大膽地觸及不應公開談論的情慾活動,有「宣淫」之虞,因而被列於禁毀之列。然而從這些殘存於世的「負面」教材,卻彰顯一些時代的風貌,有助於我們認識明清的情慾世界,並思索文化的斷裂與銜接等議題。 明清諧謔世界中的身體與情慾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在本章筆者只專注於以下較為突出的兩個面向:文化傳統與諧謔性的情色表達;性別差異、兩性關係與情色幽默。兩者分別探討涉及身體與情慾的諧謔文本在表達方式與內涵上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上的相對性。此二面向雖不夠完全,然應可幫助我們了解明清情慾文化的一些重要的特點。 文化傳統與諧謔性的情色表達 許多認知心理學家都指出幽默的表達具有一些普遍性的特點,即共通的「幽默結構」,如「範疇錯亂」(disorder of categories)、「失諧解困」(incongruity-resolution)、「另類的隱含意義」(an alternative, hidden meaning )等。這些認知上的心理機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今中外的諧謔文本。然而另一方面諧謔表達也深受文化傳統的影響。明清時期繼承數千年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當時所創作的諧謔文本自然地具有一些獨特的表達方式,而為其他文化所罕見,其中尤具特色的是文字、經典與文學傳統的影響。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根據文字學家的研究,它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三五○○年,而最早出現的型態即是表形文字。此一文字特徵促成漢字字形笑話的出現。依賴文字造型與趣味的聯想來製造笑料,在中國歷史上行之久遠,這顯然與許慎《說文解字》的學術背景與命理學中「拆字」的傳統有關。在《世說新語》、《太平廣記》等書中均有一些例子,宋代王安石的《字說》雖為嚴肅之作,然在一些人看來,也帶有諧謔的特色。明清時代的笑話繼承此一傳統,常常藉著中文象形文字的特徵,將嚴肅論域中罕言的性器官與情慾活動表露出來。例如有一則清代的笑話以「太」字來說男性的性器官,並諷刺上位者的無知與淫亂: 一太爺問書辦曰:犬字如何寫?答曰:太爺的卵子,挪在肩頭就是了。太爺說:為何要挪?答曰:太爺的卵子,六親不認。挪在肩頭,免得惹禍。(〈問字〉) 另一則明末的笑話是以「齋」與「齊」來比喻男女性器之別: 一僧讀「齋」字,尼認是「齊」,因而相爭。一人斷之曰:「上頭是一樣的,但下頭略有差別。」(〈齋字〉) 這種笑話在民國年間仍然存在,在一九二○年代上海出版的一本小說《人海潮》中有一個類似的笑話: 後來那東家又聘到一位先生,和東家同行,一樣赤腳種田的。東家問先生道:請問你先生總共識幾個字?先生道:不瞞東翁,我只識你東翁所識的幾個字。東家又問:學而時習之的「而」字怎麼解?先生笑吟吟的答道:這是我們種田人的吃飯家伙,一柄鐵耒,像不像?東家道:不差不差。又問先生道:像蓑衣一般的甚麼字?先生道:雄的「齋」字,雌的「齊」字。 文字形狀不但可以指涉男女器官,也可以用來比喻情慾活動。清初豔情小說《桃花影》以「呂」字描寫男女接吻,「玉卿……把蘭英摟住,做那呂字,蘭英便也不動」、「玉卿便挨近身側,雙手抱住酥胸,粉頰相偎,做那呂字」;作者又以「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來寫相思。下一則清初有關秀才與和尚之間相互調侃的笑話,是以「秀才」的「秀」字影射男性之間的龍陽: 有一秀才問和尚云:禿驢的「禿」字,怎樣寫?僧即應口曰:秀才的「秀」字,把屁股略彎彎便是。(你將屁股彎了送來,我僧人豈有不收之理?)(〈禿字〉) 另一則清代的笑話是以丈夫防範妻子紅杏出牆,將一個簽名的封條貼在她的陰戶上。後來妻子偷情,將此一「張仁封」的封條,撕去一半,成為「長二寸」。丈夫返家之後勃然大怒,認為此一「新」的封條有嘲弄他的陽具短小之意: 一捕役名張仁,其妻愛偷人。張仁要出遠差,甚不放心。用封條將婦人陰戶封好,寫上「張仁封」三字。張仁走後,妻仍偷人。將封皮扯去半邊只剩「長二寸」三字。張仁回家一驗,原封短了一半。大打之下說:我走後偷人,情尚可恕。你不該另寫「長二寸」三字,貼在上面。明明嫌我之短。喜人之長。豈不該打!(〈驗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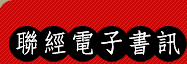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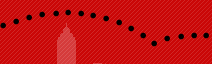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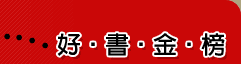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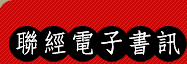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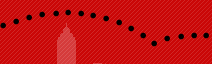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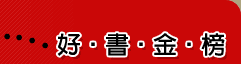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