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門內的莊子
莊子為什麼不屬於道家?
如果他不是道家人物,他的思想如何定位?
一個新的莊子圖像對於我們今日了解儒家及中國哲學,
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新視野? ※ ※ ※ 序言(節錄) 莊子研究的書這麼多,為什麼還要寫這本書?真正的動機大概只能有一個:因為我認為莊子想要傳達的消息還沒被充分地傳達出來。因為還沒被充分表達出來,所以莊子被置放在中國思想版圖上的位置可能是誤置了。也正因為有可能誤置了位置,所以莊子不屬於莊子學,戰國時期宋國蒙地的那位莊周和綿延流長的莊子詮釋學史上的那位莊子名同,卻是實異;貌合,偏又神離。就思想類型而言,兩人並不同型,最多只是近親的關係。 如果真有兩位莊子,一位是戰國時期確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莊周,一位是被詮釋出來的《南華真經》此文本上的莊子,那麼,如何解釋這兩位莊子間的異同?此工作將是本書能否處理得好最根本的關鍵。筆者這樣的對照似有機會還莊子真面目,其實也是高度抽象的產物。先別說詮釋學上「作者原意」所帶來的理論難題,即就《莊子》本身理解,也是困難重重。因為《南華真經》文本有可能不是只有一人撰寫,此書上顯現出來的莊子從來不只一種面貌,因此,也有可能不只一位莊子。 既然歷史上存在的莊周與《莊子》一書中單一而客觀的聲調之莊子都渺不可得,筆者宣稱莊子旨義尚未充分展現,所以要重探莊子原義,這樣的論斷相當危險,好像前人的莊子研究都是多餘的一樣。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不管是從前代學者的注解與闡釋,或是從近現代學者的研究當中,我個人都受益匪淺。在現代學術機制建立前的莊學傳統中,注釋是最重要的詮釋方式,歷代莊學名家通常借注釋以發揮莊子大義。時序進入 20 世紀後,中國學界有個打造新學術的大工程,現代論文形式或專書形式的莊子研究才慢慢成形。這兩個階段的莊子研究偏重面不同,但各可發明《南華》真義,筆者當然也受惠於這兩個傳統的詮釋。 近代之前的《莊子》詮釋史源遠流長,每個歷史階段提供的莊子圖像不一樣,大致說來,筆者認為我們現在對莊子的理解受到早期莊學詮釋傳統的影響最大,司馬遷、向郭(向秀與郭象)與成玄英這三位莊學早期的詮釋者奠定了後世莊學的圖像。現存最早期的三家之說皆足以自立,他們的論點能流傳至今,是有道理的。談玄理能談到向、郭層次,談何容易,向、郭的無言獨化之說提供了本書一種全體性的波狀相連的氣化世界觀。談體證工夫能深入到成玄英所述重玄之境,同樣也不容易。從成玄英到陸西星,我相信這些道士對莊子工夫論的貢獻是遠比大多數名儒高僧的著作來得大的,他們常被當代學者有意無意地視為將莊子帶上了歧途,筆者不相信此種判斷。這些丹道道士以己身為鼎爐,九轉丹成,我相當尊重他們的洞見。至於司馬遷所呈顯出來的莊子,其人顯示出一種反體制的抗議色彩,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司馬遷個人的命運,此種存在主義式的莊子對成長階段的年輕學者是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我們不會忘掉:在專制時期,莊子曾撫慰過多少飽受命運摧殘的士子之心靈。 至於近現代的莊學研究,其成績也相當可觀。如果我們以戰後華人學術社群的先秦諸子研究為例,我們發現《莊子》一書和其他先秦諸子的著作相比之下,其研究確實新義較多,尤其在語言哲學與美學的領域,當代學者的研究幫助了我們理解莊子哲學久受忽視的一面。這兩個領域久受忽視,主因是秦漢後,中國思想在語言哲學方面並沒有突破性的進展;而在美學方面,也多呈現星點般的洞見,沒有像工夫論、心性論、政治哲學方面有成系統的論述傳統。美學與語言哲學在上一世紀卻是歐美思潮的強項,名家輩出,各領風騷。國人生於斯世,「預流」其學,自然較易獲得成果。 最近十年來,莊子研究有越來越熱的勢頭,兩岸三地,皆有名家。尤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近年來持續推動國內莊子學者與歐美學者的對話,對話是實實在在的對話,甚至是火辣辣的對話,莊子被放在一個和以往迥不相同的思想冶煉爐裡伏煉,精彩四射。其後座力的震撼效果也是很可觀的,轟隆巨響之聲至今猶然在耳。雖然參與討論的中、外學者之觀點並不一致,但總體的大方向很值得注意,筆者相信一種新的莊子圖像已慢慢地浮現,這個新莊子圖像的名稱,甚至內涵都還沒有較一致的共識,但其方向大致指向一種關懷存有;強調主體的美感、語言向度;帶有一種尊重差異的民主精神之人文自然觀;而這些視角之所以成形,乃因莊子的主體是氣化交感的主體。筆者多次參與文哲所主辦的工作坊,也參與額外加碼的民宿讀書會,受益極多,這些學界畏友提供了筆者一種越來越活潑的莊子形象,一種更帶有現代價值體系:注重差異、語言風格、心物平等的莊子逐漸明晰起來。筆者非常感謝這些年來與我共學、論辯的這些國內、外友人。 筆者玩索莊子多年,早年也有《莊子》的專書行於世,但較為完整的莊子思想圖像可以說是十年來受到國內與域外同行學者的刺激而逐漸成形的。如論本書的源頭與基礎,則可溯至長久以來,我個人對形氣主體的基本關懷以及對晚明「天均之學」的重新解讀。「形氣主體」一詞也可稱作「氣化主體」,這兩個詞語雖由我所撰,卻非杜撰,它們是源自小傳統常說的「形—氣—神」之改寫。本書最早撰寫的一篇文章即探討莊子身體觀的特色,這篇文章也是我任教後,第一篇的身體論述。爾後隨著理解逐漸加深,我漸漸地趨向於認為:「形氣主體」不只是莊子哲學重要的成分,它的地位更重要,是基源本體論的核心。莊子哲學應該落實到形氣主體上解釋,從語言、技藝、遊觀到具體處世,莫不如此。我相信莊子的形氣主體是種身體理性的作用體,形氣本身孕育了語言發展、與物相契的原始秩序之潛存構造,這種形氣主體是透過氣的波動迴盪與世同在的。莊子哲學是氣化的動態的哲學,是心理合一、與世共在衍化的哲學,他的有先於無,人文建構先於解構批判。換言之,形氣主體即是生活世界的本體。我相信莊子對人文精神的貢獻,不遜於孟、荀。孟子的道德意識、荀子的文史意識、莊子的遊化意識,都是很根源的人文精神之基礎。學界對孟子的研究較透徹,莊子和荀子還大有重讀的空間。 莊子沒有說過:乃所願則學孔子或學老子之類的話語,本書卻以「儒門內的莊子」之名冠此書,這個書名顯然會帶來爭議。因為,既然莊子不以教下哲學家自居,那麼,論者如果批判道:我們其實不用承擔太多的歷史的包袱,不要用「學派」之類的術語框住他,這樣的定位似乎更合理。我同意這種批評有說服力,也很樂意拋棄歷史上發生過的學派的標籤,但對「儒門內」一詞,筆者認為依然可以成說。儒家有各種類型,韓非子說過:孔子逝世後,儒分為八,八派的具體內容很難一一指認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單一的儒家。尤其從公元11世紀理學興起以後,中國境內即有種既強調宇宙氣化、生生不息的超越哲學,這支超越哲學也是強調天人參化的形氣主體哲學,北宋與晚明的儒家多有此主張。這類型的儒家可稱為「天均哲學」的儒家,筆者相信天均哲學在當代更形重要。天均哲學的儒家走的這條路和莊子走的那條陌生而豐饒的大道,基本上是同方向的。莊子穿越了在其自體的無之意識,進入意義形式興起的「卮言—物化—遊心」主體,這種主體是人文之源的主體,莊子的立場結穴於此。莊子和天均哲學的儒家同樣主張以「有」證「無」,晚明的覺浪道盛、方以智、王夫之等人主張《莊子》具有《中庸》、《易傳》的靈魂,它們共同奠定了儒家形上學的基礎,我認為「莊孔同參」有足以成說之處。 導論
道家之前的莊子
一、前言:回到原點 本書想回到詮釋的原點,對《莊子》一書重新定位。所謂詮釋的原點也就是《莊子》此書形成之後而尚未被劃歸學派之前,具體地說,也就是孔老之後、秦漢之前的戰國中期階段的思想史位置。那個階段的一位思想家莊子生於殷商遺民組成的國家宋國,其時正是後世所謂的諸子百家蓬勃發展的時期,中原的空氣中浸潤著中國史上最富生機的思想養分,尤其孔子與老子提供的思想更成了當時不少思想家思索問題的起點。莊子有所思,有所撰述,後來經過一段我們尚未明瞭的過程,有(或有些)他的學生或私淑者承其意,續有創作,後遂被集成一部《莊子》古本的著作。在以《莊子》為名的這部先秦古籍中,莊子們(含莊子本人及其他可能的作者)展開了一種獨特的論述。秦漢以後的史家對此書的論述有所詮釋,並加以分門分派,莊子本人的思想被列到「道家」名下。本書不認為兩漢史家的歸類是合理的,所以想回到現行三十三篇本《莊子》展開的思想世界,直接依原始文本立義。然而,以文本為原點並不表示本書橫空出世,事實上,本書的完成受益於歷代的《莊子》注本非淺,本書的詮釋背後有《莊子》學史的背景。 研究《莊子》的學者通常都想回到《莊子》此原典,在原典中尋找思想發軔的原點。然而,「原點」一詞本來即神祕,預設《莊子》注釋史背景的原點更神祕。如果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一部原點的《莊子》,一部支持《莊子》原典所展現的原點之思想世界的《莊子》學史,也都不知該從何說起! 《莊子》文字極佳,卻深邃不好讀。像《莊子》這樣影響兩千多年東亞思想史的著作,其論點一再被翻新,各種詮釋觀點跨越的幅度很大,卻又常能打動不同時代、不同宗教立場人士的心靈,它的內容如果不深邃玄妙,是很難想像的。但《莊子》之難讀不僅在內容,連承載內容的文字該怎麼看,都容易有爭議。《莊子》的文字風格很強,不少謬悠之說與荒唐之言,像銀河般流動,浩瀚無垠。莊子的作品乍看之下,常不免語義跳脫,文脈多歧,所以才會有注家的作品和被注解的經典同樣難懂的情況。《莊子》的詮釋空間特別寬闊,此書的特色在此,後世的爭議也常因為此書的文字風格而引起的。 莊子的文字問題和他對語文以及整體智性的價值之定位是分不開的,莊子對語言的正面功能很懷疑,要不然,不會有〈齊物論〉裡那麼多懷疑語言功能的文句。但莊子對語言也是很肯定的,我們很少看到一位思想家像〈天下〉篇那般從語言風格界定自己的思想,在東方固然少見,在西方恐怕也不容易見到。莊子之所以那麼注意語言,甚至可說是耽溺於自己著作的語言風格,一方面固然因為天下沉濁,世人愚闇,不可與「莊語」。所以他只能使用滑稽突兀之語,以破執解蔽。但莊子所以選擇語義這麼飄忽難定的詩的語言,不純粹只是技術的理由,也不只是他是位另類的詩人,因此,握有創新語言的「詩之特權」(poetic licence)。更根本的原因當是出自他的「變化的世界觀」的考量,莊子一直很想找到一種足以和世界實相相襯的語言,也就是可以祕嚮旁通、連類無窮的語言。所以他使用文字時,喜歡於諧中帶正,於隱中帶喻,語義的游離性很強。 莊子雖然時常質疑言說的功能,但他卻有所說,至今為止,掛在他名下的文字有三十三篇,在先秦諸子當中,他的著作的文字算是多的,而且文字的文學質性極高。《莊子》一書引發了後世連綿不斷的歷史效應,歷代解莊述莊者不知凡幾,受他影響的文人、學者、平民百姓,更是多到不可勝數。所以我們在今日詮釋莊子,不能不站在兩重文本的基礎上:亦即《莊子》原始的文本以及歷代注釋《莊子》的文本。原始的《莊子》所說者已不少,歷代注莊文本說莊者更多。理論上來講,歷代說莊者的合法性要建立在原始文本的莊說的解釋上,才可以建立起來。但莊子本人已不再能說,所以莊說的原始內涵反而要透過歷代說莊者不斷地詮釋,其深層旨趣才能彰顯出來。 研究莊子學史的學者很喜歡分類歷代的莊注,陳鼓應先生最近為一本《莊子》學史的著作寫的序言中說道:中國歷代的注莊者常有以佛解莊、以《莊》解莊、以儒解莊以及以《易》解莊者,紛紜不定。陳先生的感慨自是有為而然,類似的觀察在不少莊子學的著作中也可見到。筆者很同情近賢的感慨,但也不能不指出:莊子學史觀點下的歸納是後設的觀點,詮釋者站在後出者的優勢位置,依自己理解的學派屬性,分類以往的莊注著作。這種分類有些便宜行事,可參考,但作用不大。因為如果我們回到歷代注莊者的立場,我相信大概除了少數宗教情感特強的僧侶、道士有以佛解莊或以老解莊的意圖之外,絕大部分的注家恐怕都是自認為想「表莊周之旨趣」,亦即他們都自認為自己是「以莊解莊」者。即使宗教傾向甚強的高僧高道之解莊,筆者認為他們恐怕也會認為自己的工作是要彰顯莊子的原義,而不是有意亂接異派思想之枝,以強化自家根本。只不過他們理解的莊子恰好突顯出莊子是老子原義的發揚者或是佛法東來之前的先行者,其旨歸剛好可以和佛老的真諦相互發揮罷了!如成玄英就認莊子的意圖本來就想「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所以他才依此一線索,以老子義理注解《莊子》。即就本書而論,筆者的解莊當然也自認為是「以《莊》解莊」。 我們探討《莊子》首先要面對的是一部《莊子》文本與歷代釋莊、述莊者合構成的一部波瀾壯闊的莊學演變史。如果絕大部分的注莊釋莊者都自許為「以莊解莊」,那麼,我們如何分辨有效的「以莊解莊」以及無效的「以莊解莊」,這樣的問題就出現了。討論《莊子》詮釋的有效性,我們首先會面臨兩個很棘手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陳年沉痾。一是《莊子》各篇章的作者問題,《莊子》此書就像一些先秦的典籍一樣,它可能成於眾人之手,而不是出自單一作者,因此,如何分辨何篇是莊子原著,何者是後人所加,問題就發生了。這件事糾纏已甚,極難分疏。另外一個問題是《莊子》的語言風格極特別,基本上,我們可以確定莊子對於知識論導向的敘述極無興趣,他甚至對語言的傳達功能都很懷疑。因此,頗有莊學名家認為莊子如同後世禪宗,其語詼詭譎怪,正言若反,其旨義不能依一般日常語言下判斷。因此,《莊子》篇章中的語言到底是直敘的?反諷的?或是詩意的?其性質不免費人猜疑。 一部《南華》,到底有幾位作者,已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在此文本身上又附著了歷代流傳下來的層層疊疊的注解作品,這些衍生出的文字有多少是文字障?有多少是文字般若?又是個問題。原始文本須仔細解讀,這批歷代流傳下來的業績本身也亟待清理。筆者選擇的標準在哪裡?這種質疑可想像地一定會出現的,筆者不能不答覆。筆者還是回答道:依然是要「以莊解莊」。不管「以莊解莊」在實際的檢證標準上是如何地難以檢證,在詮釋學的理論設定上是如何地冒風險,但就作為行之久遠的注解策略,此一詞語仍然相當地有效。筆者的「以莊解莊」將是回到莊子的原點,回到莊子的原點也就回到被漢人分家分派之前的《莊子》文本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司馬遷,沒有劉向,沒有班固。換言之,也就是沒有「道家」一詞。眾所共知,先秦時期只有「儒」、「墨」兩家有學派之名,「道家」就像其他的學派名稱一樣,都是秦漢後興起的概念,是追溯出來的。當我們將道家還給漢代史家,將《莊子》文本還給莊子,我們就得面對一個尚未被定性、定名的原始文本,它呈現自己,自己解釋自己。問題是:經典不會只是「在其自體」(in-itself),它永遠也要「對其自體」(for-itself),我們該如何理解它? 面對著這個未被歸類的文本世界,筆者想嘗試找到一個設想中的《莊子》作者自己所表述的著作旨趣,在下文的分析中,我們將會發現:他的意圖會揭露《莊子》文本有個形上學的原點,《莊子》一書是依形上學原理而不是歷史原理展開的文本,這是第一個原點。其次,由於哲學興起之前通常有個神話的時期,神話題材與哲學議題之間常有關連,莊子可以確定是先秦諸子中最具神話精神的哲人。在神話世界中,發生於開闢時的「彼時」之剎那,乃是一切存在之根源或基礎。筆者相信宇宙開闢的神話母題是莊子論述的「太初本體論」的原點。在形上學的原點、太初本體論的原點外,筆者將會以「形氣主體」作為基源本體論的原點,借以補充形上學的原點。以上述這三個原點為核心,筆者認為《莊子》一書的內容雖然繁富,卻有軸心。莊子既站在孔、老之後的思想風土上回應孔、老的議題;也站在繼承殷商巫文化的宋國這塊土壤上,回應神話的啟示;而莊子之所以能回應遠古的與近世的文化傳統,乃是他對人與世界的本質皆作了根源性的批判,他的新的主體範式全面性的安頓了人的經驗世界。 本書以「儒門內的莊子」名書,既然用到「儒」字,就很難不把學派的因素帶進來,也就不可能不是個學術史的論述。如果有論者從學術史的角度下此評斷,筆者同意這種質疑是可以成說的。但本書的意圖恰好不屬於狹義的學術史,筆者所以透過形上學的源頭、神話的源頭、基源本體論的形氣主體之源頭,以界定孔老,主要是這種連結也見於《莊子》原本,筆者可以說是接著講,論本書的根本旨趣,筆者只是希望透過多重管道,指出莊子提供我們一種足以作為有意義的人文精神的主體觀,這種新的主體範式代表的是一種積極哲學的型態,這種積極哲學的主體不見於漢代以後的道家名下的莊子。所以我們只有逆流而上,神與《南華》遊,才有機會切入箇中三昧。 內文選摘(節錄)
壹莊子與東方海濱的巫文化
一、前言 巫在早期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早自近代國學奠基者的劉師培、王國維以下,已一再提及斯義。巫是上古文獻中所能見到的最重要的宗教人,也是涵義最廣的宗教人。如果我們認為在文明發展的初階,所有的知識都離不開宗教的母胎,宗教的知識總會以或隱或顯的方式滲透到所有的文化的分枝的話,那麼,中華文明當也不例外。筆者相信:最早的歷史、地理、政治、文學、戲劇等等的知識都可看到巫文化的胚胎。 本文想探討莊子與巫文化的關係。莊子為公元前 3、4 世紀的哲人,其時「道術(已)為天下裂」,這是史家所謂「哲學突破」的時代,巫已很難再掌握太多的知識,因此,也沒有那麼大的文化詮釋權力。但筆者認為巫文化在莊子思想仍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莊子不但借助巫文化的因素當作他敘述時的核心架構,莊子思想的核心義往往也是來自於對巫文化源頭的轉化。筆者嘗試作文化解碼的工作,此工作一方面探索莊子思想的起源問題;一方面也希望探觸到從莊子思想的起源到其思想本質的建立之間的轉換過程。這樣的轉換過程包含了敘述時所使用的巫文化因素,也包含了從巫的精神內涵到莊子體道論的轉化。本文由於篇幅所限,重點將落在起源的問題上面。 二、《莊子》古本與巫 關於莊子思想的起源問題,從《莊子.天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以下,言之者多矣,解釋相當紛歧,據筆者粗淺的統計,比較流行的說法大概有下列各種:「歸本於老子」(司馬遷)、「源於太一」(莊子本人)、「源於儒家」(韓愈)、「源於楊朱」(朱子)以及「自成一家」(郭象)諸說,這些說法雖然證據強弱不同,但大體可說言而有據。其中,筆者認為論證最薄弱者當是「楊朱說」。此說雖得到一些大有來歷的人物之支持,但這樣的說法不管就外在的歷史淵源或就內在的理論考量,都找不出較強的證據足以支持此說。「自成一家」之說最難反駁,但這樣的解釋事實上也可以說沒有作出太多的解釋。沒有人會否認莊子已成一家之言,但我們可以反過來想:沒有任何思想是獨特到自創己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任何獨創的思想總需要滋養此思想之傳統,所以「自成一家」與影響兩說並不構成任何互反的關係。這個理論最多只能說明莊子綜合百家,而無一家可歸納之。「太一說」則是種形上學的提法,這樣的解釋可以給世間的任何學問一種形而上的保障,但此說無關史實。「源於老子」之說頗有文獻之依據,歷代提出此說者的公信力都比較高。但此說依然僅能解釋莊子思想之部分因緣,而不足於解釋莊子與老子兩者思想之差異。至於「莊出孔說」,此說如作為哲學或思想史的解釋,其言論似有一獨特理路。但作為歷史的解釋,此一說法似乎不太能成為有力的論述。
上述所說的幾種論點之是非得失,牽涉到歷史文獻的諸多檢證,枝蔓甚廣,當專文檢證,此處姑且不論。「莊子思想起源於巫文化」的說法當然不像上述諸說那般受到注目,但自從聞一多提出「古道教」之說後,莊子與原始宗教的關係已不是太陌生的子題,《莊子》書中蘊含的神話題材,現在更是日益受到學界重視。然而,從巫或薩滿教(見下文)的角度重新詮釋《莊子》,此工作恐仍大有發展的空間。筆者作的這個工作當然無法推翻或取代前人所提的各種「源出」說,筆者也不作此想。本文的意圖只是想突顯《莊子》一書較少被正視的「巫」文化之因素,《莊子》書中這種類型的巫文化因素之內涵及其轉換,不管對我們想了解莊子本人的思想或對我們想了解先秦道家精神史變遷的人而言,應該都會帶來一些啟示。 本文想從「巫」的角度重新探討莊子思想的起源,但本文的前提頗涉曖昧,因為「巫」的角色甚多,涵義甚廣。《說文》釋「巫」字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許慎作的雖然是字詞的解釋,但他指出巫的兩大特色:(一)溝通神人,(二)巫是舞藝(廣義來說,藝術)修養甚高的人,這兩點都極中肯。晚近研究巫的學者,其主要論點往往亦不出此兩者。但這兩點的具體內涵需要再擴充,如「事無形」一詞尚可包含祭儀、巫的人格特質等等。舞藝或藝術方面,更宜擴大到包含天文、醫學等等巫師專長的技藝。至於「巫」是不是專指女性,這倒不一定。《國語》雖有「在女曰巫,在男曰覡」的說法,但更常見的情況乃是:巫為男巫女巫之通稱。 近人對巫的解釋日漸豐富,但由於記載「巫」的典籍通常離巫文化最盛的時期已遠,而且「巫」本身的功能也不斷的分化。就最廣義的觀點來說,它可以指涉擔任一切宗教職務的人員,「巫」與「祝」、「宗」、「卜」、「史」、「醫」的工作往往重疊,他最重要的特色遂變得隱沒不彰。因此,中文原始材料及第二手研究對「巫」的解釋固然是我們探討中國的巫文化時最重要的依據,但就理論架構而言,我們不妨參考晚近學者對薩滿教的解釋,然後兩者對勘,如此或可突顯在諸子興起前甚至周公制禮作樂前的一段思想史之特色。 薩滿教當然也是個內涵複雜的詞語,我們不妨參考耶律亞德(M. Eliade)、佛爾斯脫(P.T. Furst)及相關材料,羅列其特色如下,以便討論: 1.薩滿式的宇宙乃是巫術性的宇宙,而所謂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環境這種現象乃是巫術式變形的結果,它的宇宙一般分成三層,有時還有四方之神或四土之神。宇宙的諸層之間為中央之柱(所謂「宇宙軸」)所穿通;這個柱與薩滿的各種向上界與下界升降的象徵物在概念上與在實際上都相結合。 2.薩滿教相信人和動物在地位及性質上是平等的,他們可以相互溝通。而且,人與動物之間可互相轉形,自古以來,人和動物彼此即可以對方形式出現。薩滿們一般都有動物助手,這些助手可稱作助靈,助靈可幫他到彼界作神祕之旅。 3.靈魂可以與身體分開並且可以到各處旅行,甚至旅行到天界或地下的鬼魂世界。 4.自然環境中的所有現象都被一種生命力或靈魂賦予生命,因此在薩滿世界裡沒有我們所謂「無生物」這種事物。 除了上述四個特點之外,薩滿教當然還有些重要的特性,如不怕火燒、靈魂或生命力常駐骨頭,以及嗜食麻醉性強易導致幻象的植物等等,但上述四個要點:空間形式、空間的鳥獸、主體、世界的本質,與我們要探討的主題最為相關,也特具思想史趣味。第三點離體遠遊的人格型態更是特殊,它與後來佛教與理學追求的圓滿人格相去絕遠,但在國史的發軔期,它卻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將它特別標明出來。本文下文所謂可以和莊子思想相互發明之「巫」、「巫教」、「巫文化」,即指此解體人格型態的薩滿及其文化母體薩滿教而言。 現行《莊子》一書,直接提到「巫」的地方不多,只有三處。為什麼巫文化與莊子頗有交涉,但「巫」字在《莊子》書中卻不占重要地位?我們現在想到這個問題,覺得很棘手。然而,如果我們是在一千五百年前作這個工作的話,情況應該就會好很多,因為當時的《莊子》版本和現在流行的郭象版不一樣。郭象版三十三篇,但先前的《莊子》版本並沒有統一,班固、高誘、司馬彪等人所見的《莊子》是五十二篇,郭象認為這五十二篇當中,頗有些篇章是「一曲之士,不能暢其弘旨,而妄竄奇說」的偽作,因此,將它們刪掉了。郭象還特別指出五篇的篇名,並說這些偽作「或牽之令近,或迂之令誕。或似《山海經》,或似《占夢書》,或出《淮南》;或辯形名,皆略而不存。」簡言之,我們現下看到的是淨化的簡本,是郭象依他的眼光判斷所抉選的產物。郭象說的「或出《淮南》,或辯形名」這類的內容不在我們的考量之列,但「或似《山海經》,或似《占夢書》」這類的文字卻不能不令人眼睛為之一亮,因為《山海經》本來就是部巫書,而占夢原本也是巫的看家本領之一。如是說來,《莊子》五十二篇本應當保留相當多有關巫風的文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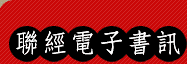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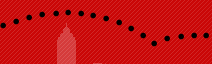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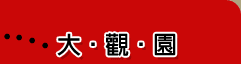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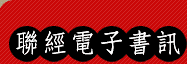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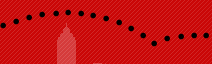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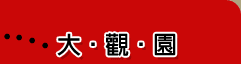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