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大掃除時,我發現家裡有個餅乾裝的鐵盒,打開一看,裡頭是一對蛾的標本。但保存不慎,已經有些氧化、破損。我問父親這對蛾的標本從哪裡來的?父親說,那是村裡著名旅社的第一代阿公十幾年前送來的。當時旅社已經傳承下去,他便自己一個人住在山上的房子。
一天,阿公看見一對長得極其漂亮的蛾停在家門前,似是一公一母。他盯了一會,很是喜歡,沒有打擾,默默地進了家門。隔天,正準備出門,卻發現那對蛾已經雙雙仰躺在門前走廊,沒了動靜。於是,阿公將那對蛾裝進餅乾鐵盒裡,帶下山,問我父親是什麼種類。
父親後來查到了,那對蛾叫作「姬長尾水青蛾」,是台灣特有種。阿公知道後心滿意足,便把鐵盒送給我父親,說這對蛾至死都情深,值得人類學習。於是,父親也將鐵盒收藏下來,一放就放了十幾年。
●
阿公的旅社名叫順泰,約1970年代營業至今,整棟旅社十幾個房間,四、五個出口,樣式一致的長廊,就像個大迷宮般。每天都有村人在裡頭穿梭,有旅人在櫃台前準備入住,偌大的建築不曾有過關門的一刻,也因此成為我們這些孩子玩耍、追逐、捉迷藏的所在。當時我們最常爬到頂樓眺望村子的山景,或惡作劇吼叫街上同學的名字,不知不覺日頭就掛到中央山脈,一會兒掉入山中。
旅社如今傳承到第三代,第三代的老闆與我自小相識,他返鄉接下旅社後,學習裝潢、水電與木工,刻意保留老旅社的外觀,一點一滴地改造旅社內部的模樣,順泰也因此有了老櫃台與新櫃台。
我曾在小時候玩躲貓貓藏進老櫃台,當時旅社的阿公坐在櫃台邊,一邊擋著,一邊什麼話都沒跟玩伴們說;我就在櫃台裡,聽他們跑遠又跑近的聲音,憋笑憋得不斷發抖。但我沒想到,過一會兒整棟旅社變得寂靜無聲。我悄悄地將頭伸出櫃台,左右看去,都沒有同伴們的身影,這才發現他們找不到我,竟然乾脆放我鴿子。
直到年長一些後,我才知道順泰阿公的故事。他是宜蘭人,世代務農,當時聽人說花蓮機會多、土地多,去那兒會有自己的一番天地,便動念到花蓮謀生。但那個年代去花蓮只有兩條路,一條走陸路,穿過九彎十八拐的顛簸;一條走海陸,航經清水斷崖的險峻。
他叫我猜他怎麼來?我問他:那你怎麼來?
「我騎單車,騎單車去花蓮。」他一面說,一面拿出一張老照片,照片上是他牽著單車和自己的孩子並立於豐田的街口──那一年他真的騎上單車,一路往南,經過九彎十八拐、清水斷崖。當時單車笨重,上坡騎不動時他就用牽的,下坡太快時就用腳擦著地協助煞車;遇到有車要交會時,他得趕緊與單車一起「陷」進山壁裡,看著那時路寬只有三、四米的九彎十八拐,車輛貼著他的鼻尖劃過──敞開的小公車車窗,傳出來往蘇花的旅人們在車上的汗燜味、食物味與菸臭味,偶爾也會聞到有人吐在車上的酸臭味。
之後他到了花蓮,仍然持續往南騎,不斷尋找可以落腳的地方。終於騎到豐田,他又累又渴,停在街邊歇息,有人主動端了碗水給他。他喝完一碗又要一碗,兩碗水下肚後,他發現自己已經累得騎不動。他告訴自己,承著兩碗水的恩情,他就要在這裡定居。
●
這件事情他到晚年都還常說。那時他常穿著POLO衫,身上總有張勸善文,用黃色A4紙張印製且摺疊整齊地塞入上衣口袋。若遇到有人與他攀談,他就會抽出一張遞給人,要大家記得對世事充滿感激。後來他不太記得我是誰,但總不忘對我說:「要與人為善。」語畢便給我一張勸善文,我從他手上收過六張,第六張是最後一張,之後阿公便離開了。
今年六月底,與我同住的妹妹、妹夫、外甥女相繼確診。為了避免我們一整家人都被隔離在家,第三代的小老闆開了一間單人房,讓我住了近兩周。要入住的第一天,我在午後拿著行李走進旅社,發現有幾個孩子鬼鬼祟祟地在旅社中玩耍,看到我走過去便嚇得四散奔逃。
我先前只注意到今日特別炎熱──又是夏天了;但,原來今天還是小學放暑假的第一日。已經不再將七、八月稱之為「暑假」的我,這時也難免被孩子們染上歡快的氣氛。老旅社的後門面西、正門向東,餘暉貫穿了整棟旅社的走廊,應該是極美的模樣,但我卻想起了童年的午後在旅社找不到玩伴們的驚慌。
進到房間,我將背包幾天份的衣服、五日的快篩劑,還有一整盒的口罩和酒精一字排開,那時我才意識到──我竟有一天成為這裡的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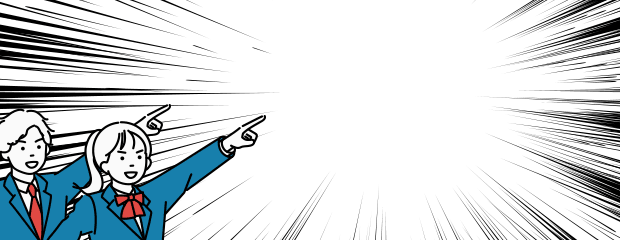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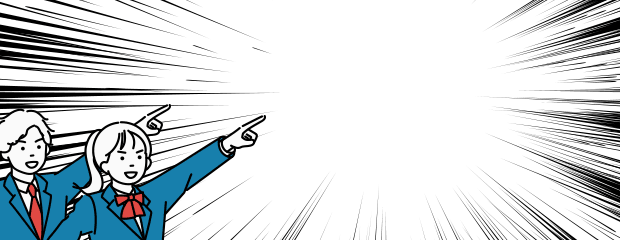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