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一個普通市民眼中的戰爭、社會與國家是怎麼一回事?
身處社會最基層、無法抵抗權力擺布的普通士兵,
面對一場不知從何而來的戰爭,如何影響他的一生? 我們讀過許多由知識分子撰寫的二戰回憶,固然是可貴的文獻,卻只是「少數」、「特定面向」的視野。《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站在下層庶民的立場呈現日本社會「真正多數人」的二戰及戰後掙扎求生之體驗,打破「虛假的社會想像」,提供我們截然不同的視野及思考方向。 第三章 西伯利亞/小熊英二(Eiji Oguma) 二、國家應負起的責任 一九四五年到四六年的冬天,處於最惡劣狀況的不限於謙二所處的收容所,幾乎所有拘留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載。發生這樣的狀況其實有幾個理由。 首先,日本敗戰之後,蘇聯的經濟也處於相當窘迫的狀態。德蘇戰爭中蘇方的陣亡人數,從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說法都有。蘇聯人口於一九四○年有一億九千五百九十七萬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則為一億七千三百九十萬人,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陣亡者約有三百一十萬,約占一九四○年日本內地人口七千三百零六萬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蘇聯領土西側的工業地帶與穀倉地區因為德軍占領後採取焦土戰術而遭到破壞,雖說蘇聯最終戰勝,但經濟狀況也陷入窮迫之中。因為陣亡者過多,許多村莊的男子出征之後幾乎無人歸還。在一九四○年,集體農場的男女勞動力比率大約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則轉為一比二十七。 需要將日軍俘虜當成勞動力帶走,或出現這麼多同情謙二這種年輕人的俄國女性,都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背景。謙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為了作業的緣故,曾經與幾個俘虜夥伴一同住宿在俄國的某戶民宅。一位應該是戰爭寡婦的女性帶著一個小孩,過著兩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舊了的那一套,令人驚訝地房內真的是家徒四壁,沒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間竟沒有床舖,睡覺時他們只把外套披著躺下。好歹總算還有個壁爐,除此之外就是幾樣煮飯用的鍋子與餐具而已。他們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從戰前到戰後,在日本還沒見過這種生活狀態。 因為如此,原本應該供給給俘虜的物資,便遭俄國人盜賣。已經不足的食糧與燃料經過盜賣後,送到俘虜手中時數量更為稀少。 送來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遭到盜賣,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送往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文件上雖然都記有運送噸數,但貨車或卡車的司機會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半路卸下這些物資,剩下的才會送到我們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幫助運送煤炭,還幫忙盜賣這些物資。俄國人司機利用我們,在自家與有協議的住家卸下煤炭。至於減少的數量,只要送往目的地工廠時不要減少過多,領取一方也不至於有意見。戰爭時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為統制經濟的緣故,難以取得物資,大家都在盜賣與偷取物資。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出過命令,必須送達規定量的食糧給俘虜 ,但實際狀況則如上所述。 何況,蘇聯這個國家在對日戰爭時,也掠奪了大量物資。謙二曾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貨物場,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整理工作。 掠奪物資堆積如山。關東軍軍需物資的電纜線、鋁條、電話機等等,由貨車整車運來,就這麼卸下來堆放著。當我找到裝在進貨用箱裡、多達數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門用把手時,只能感到一陣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麼就拿走什麼吧。 我們也偷走了一些鋁條去製作湯匙。當時俘虜的幹部曾經交待,如果看到鋁條就拿些回來,送到鍛造房後,那邊的俘虜便鎔鑄做成盤子等餐具。不管是我們自己,或者是俄國人,大家都把竊盜視為理所當然。 在整理堆積如山的大量物資時,有人就說:『就是靠這些才打贏德國的吧。』蘇聯士兵作法蠻橫,但充滿幹勁,上級下達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衝勁完成。如果是在日本軍隊,上級胡亂給了辦不到的命令,下級絕對不會有那種幹勁去完成。 對照於民眾生活的窘迫,謙二對蘇聯的強大軍事力量也留下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東方駐紮著蘇聯的戰車部隊,停駐著體積龐大砲身修長的T34戰車。「被派出工作時有機會接近一看,內心覺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戰車不僅小,而且只是用鉚釘把鐵板釘在車上當裝甲而已,根本完全無法戰勝對方」。 而且蘇聯的軍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受到盟國美國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蘇聯軍隊卡車時,對於他們使用這麼大的卡車感到非常驚訝。前輪是二輪,後輪則兩兩成對共四組,全部共十個輪胎的卡車,輕輕鬆鬆便爬上山坡,相較之下日本卡車實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經常看到類似的卡車,引擎蓋上印著USA STUDEBAKER字樣,才知道這是美國援助的物資。『如果沒有美國援助,蘇聯應該會輸給德國吧』,俘虜間聊天時經常互相恨恨地這麼說。 對於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蘇聯人似乎也充滿不滿,只是表面上沒說出口。 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個表情嚴峻的俄國人,在我們作業中靠過來攀談,用俄語說:『史達林,不好。』他與我們也沒多熟悉,會對我們說這些,大概是因為無法與俄國人討論這些事情吧。在史達林時代,說這種話如經告密,就會被送到集中營去。 此外,蘇聯方面對於接收俘虜一事,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等戰俘抵達之後才開始整備戰俘營即是一例;且不僅發生於謙二的戰俘營,在其他各種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蘇聯在沒有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下,便強制帶走這些人,當作自國的勞動力。 俘虜們在戰俘營雖然有領到冬季衣物,但其實這些是蘇聯軍隊從日本軍擄獲的防寒衣物與防寒靴,在西伯利亞根本不夠保暖。 日軍的冬季衣物跟蘇軍相比,實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為了止滑在靴底打上鉚釘,但寒氣卻會隨著鉚釘直傳腳底。蘇聯的防寒帽都有兩層,日軍的僅有一層。蘇聯人常說,在西伯利亞如果額頭受寒,就會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著這種裝備與蘇聯軍隊作戰。日軍曾經出兵西伯利亞,理應學到一些經驗與教訓,真搞不懂軍部的人究竟在想什麼。而蘇聯方面似乎也不知道這種狀況,從隔年起,大家都想換用蘇聯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據謙二的說明,最初的冬天,戶外作業時不斷出現人員凍傷。但從第二年起,根據哨兵所的溫度計,早上六點如果溫度低於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戶外作業,蘇聯方面也開始再三注意預防俘虜凍傷。「恐怕俄國人也沒想到,日本士兵如此無法抗寒,竟然造成了這麼多犧牲者」。 在這種準備不足與惡劣待遇之下,自然招致俘虜們不想勞動且效率低落的結果。根據蘇聯內務省預算收支統計,由俘虜勞動獲得的收入,不僅無法維持管理費用,一九四六年度還出現了三千三百萬盧布的赤字,必須由聯邦支出預算來彌補。 提出這個數字,並非想為蘇方辯護。畢竟當蘇聯決定利用俘虜進行強制勞動,就應當負起責任,但蘇方卻未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也沒有勞動計畫,在這種情形下移送六十萬俘虜,只能說是異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導致的結果,除了非人道的處境之外,這種愚行還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便俄國人個人不帶惡意,但國家仍難辭其咎,必須負責。 部分俄國歷史學家曾經提出,「與遭德軍俘虜的俄軍受到之虐待相較,蘇聯對日本人俘虜的處置已經相當人道」,或者「關於俘虜待遇,因為蘇聯並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條約,所以無須遵守俘虜規定」等見解 。根據蘇聯中央政府的指示,給予俘虜規定量的食糧,支付他們薪資,甚至有俘虜能到市集購物,這些情況確實可能存在,但並無法成為否定日本俘虜境遇悲慘、被當作奴隸操用的論理根據。 不過同樣地,這樣的指摘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方面。雖說大日本帝國統治朝鮮時出現赤字,但這並不能當作是日本曾在朝鮮施予善行的根據。而日軍在亞洲各地掠奪當地居民的物資,加上輕視補給與管理拙劣,最終責任仍應在於把戰線擴大到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線的士兵們不懷惡意,但國家仍責無旁貸。而與上述俄國方面歷史學家相似的發言,是否也存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這點諸位不妨試著思考看看。 三、飯盒是活命的基礎 在這種狀態下,被擺在窘迫蘇聯社會最底層的俘虜們,他們的生活也達到一種極限狀態。根據謙二的說法:「完全就是活在原始時代。」 抵達戰俘營時,謙二還穿著日本軍服,身上帶著的物品只有飯盒、水壺、用舊的軍用毛毯、以及背包中稀少的日用品。雖說日用品,但既沒茶杯也沒牙刷或餐具,連換穿的內衣都沒有。 當時帶些什麼東西,已經不太記得,但有軍用襪與裁縫袋。裁縫袋是外祖母小千代當我入伍時讓我帶在身上的。後來起了非常大的功效。因為沒有任何換穿衣物,衣服破了就得自己縫補。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亞寒冬中,衣服穿不好是會要人命的。縫線沒了之後,就從不穿的軍用襪上拆線來用。 特別是縫衣針,在戰俘營算是貴重物品。一九四六年夏天之後,有些手巧的俘虜會利用打火石自行製作,也有人利用取得的鐵絲磨針。不過將鐵絲磨尖雖然不難,但該如何在後端打洞讓線穿過,卻沒那麼簡單。因為自己帶著針線,所以無須苦惱這些問題。 破布也算是貴重物品。衣服破掉時,如果不加上一塊補釘就直接封補,很快又會再度破裂。可是可以當作補釘的破布在戰俘營中難以取得,大概都是外出作業時,與其他覺得對生活有幫助的東西一同撿拾回來。 另外在謙二的雜物背包中,除了幾件僅有的物品之外,還有一面日本國旗。那是入伍的時候特別配給的物品。在移送往西伯利亞途中,謙二一直把這面日之丸國旗「當作洗澡時的浴巾」來使用。 那面日之丸,在抵達戰俘營約十天後,就被蘇聯兵沒收了。蘇聯士兵之間一直認為日本士兵帶有值錢的物品,不斷以檢查的名義進行沒收。 原本他們也是窮人,擁有的東西大概不會比俘虜多。當我們外出服勞務作業時也知道,蘇聯領土內的人們似乎連像樣的衣服都沒有,甚至有些蘇聯女性還穿著從滿洲運來的日軍軍服。沒收日之丸國旗也不是為了思想上的理由,大概只是被他們拿去當成圍巾或頭巾吧。 我們這邊對於沒收,也不會去聯想什麼思想問題。不少日本軍的軍官回憶錄中寫過,自己的手錶遭蘇聯士兵取走,我從開始就沒戴錶,畢竟新兵連看錶的時間都沒有。 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中有兩幢木造建築物。謙二等人入住的兵營是天花板較高,類似倉庫的平房建築物,裡面大約收容了五百人。另一幢建築則有大隊本部、廚房、醫務室、食堂、蘇聯方面的辦公室等,是一幢較小的建築。但謙二一行人剛到此地時,只覺得這些建築物「就像廢棄物放置場一般」,根本不具備任何機能。因為食堂無法使用,用餐時都將雜燴粥裝在木桶中,拿到兵營內分配。 謙二入住的兵營中備有讓俘虜們睡覺的木造居住空間。完全沒有個別空間,只有像「養蠶架」的大型三層床。俘虜們便擠在上面,爬上去後若不盤腿坐著,頭立刻會碰天花板。兵營中的照明,只靠著一顆無罩外露的電燈泡。 兵營中有兩組三層床,一組可以睡上一個中隊,約兩百人。每個臥鋪分給七、八人使用,每個人大概只有五十公分寬的空間,肩並肩便會互相擠碰,所以俘虜們彼此都頭腳交錯著睡下。 臥鋪由圓木背板組裝而成,背面搖搖晃晃,這種只是由背板排列而成的三層床並不牢固,只要一個人翻身,周圍其他人的背板都會跟著搖晃。雖然集合大家手邊有的毛毯鋪上,冬天仍冷到無法忍受,必須穿著外套才能入睡。謙二一開始睡在臥鋪的第三層,後來搬到第一層,上層的木屑與灰塵老是灰撲撲地不斷落下。 西伯利亞的晚上,溫度會降至零下四十五度,如果沒有暖爐便無法存活。戰俘營的兵營雖然也備有壁爐,但又小又缺乏燃料。他們度過的第一個冬天,每個人擁有的寢具只有一張毛毯與一件外套,感到寒冷的時候,得靠著旁邊俘虜的體溫彼此取暖。 服裝就那麼一套,無可替換。最初的冬天為了禦寒,會將裝水泥的紙袋切出可以伸出手腳的洞後穿上取暖。紙具有隔熱效果,多少能夠保暖。襪子破得很快,需要拿破布等物品包纏以防凍傷。 赤塔沒有上、下水道,俄國人也從流過市鎮南邊的河川汲水使用。先以大桶到河川裝水,再以雙馬車載往市鎮巡迴分配,各個家庭以此作為生活用水。在戰俘營也設有大桶存水使用。家庭用水的廢水都丟在家中,但隆冬時節往往迅速結冰。 因此水也屬於貴重物品,如果沒水,俘虜連洗臉都沒辦法。喝的飲料只有早上提供的熱湯。第一個冬天只能任頭髮與鬍鬚不斷生長,得等到翌年夏天較有空閒時,才能到赤塔南邊的河川去清洗內衣,謙二說最初的冬天沒有清洗過衣物的記憶。雖然如此,因為濕度很低,幾乎沒有流汗,加上營養不良導致新陳代謝緩慢,幾乎也沒什麼體垢。 因為只有一套衣服,所以開始出現蝨子。星期天是唯一不須勞務作業的日子,因此上午除蝨子成為例行公事。在謙二所在的戰俘營,雖然沒發生過因蝨子傳染斑疹傷寒的狀況,但其他戰俘營,的確發生過因傳染病而導致許多俘虜倒下。 抵達戰俘營沒多久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夜晚,在完全沒有告知戰俘的情況下,把大家都趕出戶外。在不安中,大家被帶到一處公共澡堂,該處有一個大型熱氣消毒室,將俘虜們脫下的衣物進行滅菌消毒,同時大家也利用水栓流出的一點熱水擦拭身體。但因收容所的衛生環境並無改善,所以這種除蝨作業也只有短暫的效果。而且當大家回到戰俘營,立刻發現所有行李都遭蘇聯士兵翻搜過,鋼筆等值錢物品都遭取走。「自己的東西幾乎都沒被偷走,
不過兵營整個被翻得一團混亂」。 謙二的視力大概只有○.五,進入軍隊後許多時間需要看清遠處,因此他有戴上眼鏡。但在西伯利亞時眼鏡破了,之後便沒有眼鏡可戴。不過,謙二說:「這種事情還算不上辛苦,比自己視力更差的大有人在,也不記得聽過有人抱怨不便。」 在戰俘營最初的兩個月,飲食幾乎都是水與由高粱做成的俄羅斯麥片粥(Kesha)。謙二形容是一種「像日本粥的乾爹」般的食物。其他的食材還有稻米、小米、玉米等,謙二說:「大概都是從滿洲來的戰利品,畢竟自己也在黑龍江畔幫忙裝卸,親眼見過。」第二年開始,除了穀類的雜燴粥之外,也會放入鹹魚一起熬煮,有一段時期還出現過支援蘇聯的美國製醃牛肉罐頭,最初的冬天完全沒有這類物品。 進入一九四六年之後,除了早餐與晚餐的雜燴粥之外,還能領到黑麵包作為外出勞務作業時的午餐。但因早餐分量很少,大部分時候會把黑麵包與早餐一起吃掉。有時想忍耐著不吃,但禁不起誘惑心想咬一口就好,最後終究停不下來,全部都吃掉了。 雜燴粥由俘虜們組成的炊事班調理,大家各自拿著飯盒去盛領。蘇聯方面並未提供餐具,俘虜們拿著自己帶來的便當盒,以及外出作業時偷來的鋁條、木片製成的湯匙食用。靈巧的人製作的湯匙相當好用,連黏在飯盒上的如漿糊般的部分都可刮起,但謙二的湯匙卻只是個像小破片般的東西。 飯盒是活命的基礎,什麼都可以捨棄,但大家絕不會放棄飯盒。甚至到了自己要回日本時都還想帶著回家的程度。其中有些人到日後也一直保存著自己的飯盒。第二年開始配給美國製的醃牛肉罐頭,大家也拿著空罐當餐具。前往蘇聯軍官家中幫忙清掃排水時,經常會清出空罐,有不少人也會撿回來當餐具使用。 日軍的飯盒有被稱為「single」的單層式,以及可以放副食稱為「double」的雙層式兩種。兩者的容量有所差異,不管如何公平分配食物,總會有差異。在一些西伯利亞回憶錄中可以讀到,許多俘虜會敲打飯盒底部使其隆起,企圖多少增加飯盒的容量。 謙二待的戰俘營,關於食糧配給採用了一套自己的方式。大家不是拿著各自的飯盒去盛粥,而是集合大家的飯盒後,全部分盛好,再分配給每個人。 分配餐飲時,大家眼睛都睜得像牛鈴那麼大。所有人的餐盒都聚集在一處,接著由炊事班運桶子來到小隊上分配雜燴粥。雖然分配時都盡量公平,但所有人都張大眼盯著,因此總會有人抱怨分配少了,在食物分配上,從未少過紛爭。春天之後想辦法偷了些蘇聯的物資,替每個人都做了鋁製餐盤,大家都有相同的餐具,畢竟不讓大家自己從炊事班手中拿到食糧,紛爭永遠不會結束。 即便如此,在謙二戰俘營的俘虜們,並非維持原本部隊型態,而是混合編成的聯隊,所以食糧分配算相當平等。依照原部隊編成進入戰俘營的部隊,軍官或士官們手中握有食糧配給的權力,下級士兵──特別是新兵──往往最後才能領到食物。這種狀況也形成俘虜間「民主化運動」抬頭的背景,這會在下一回中說明。 四、對某位青年的追憶 如前所述,死在列車上的俘虜,全員都還目送他到墓地安葬。但之後俘虜們便不再有這樣的餘裕。 隨著氣候逐漸嚴酷,大家也開始了幫火力發電廠挖掘溝渠的作業。火力發電需要從河川汲水,煮沸後推動發電渦輪機,但在水循環期間取水溝與排水溝會凍結。為了讓水能流動,必須挖掘溝渠,打碎結冰。為此動員了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五百名俘虜中的三百名,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持續在野外進行作業。 大家在河邊的土地上以鐵製圓棒敲擊冰塊,但是土壤與砂礫混合凍結,狀態就像混凝土一般堅硬,不管怎麼敲打,一天頂多只能敲出十公分左右。零下四十五度時,沒有什麼濕氣,呼出的水蒸氣立刻凍結,變得如鑽石粉末一般。在荒郊野外極度寒冷下作業,加上空腹與營養失調導致的寒冷與疲勞,陸續造成了人員死亡。 為了抵抗飢餓感,在有些俘虜之間會利用一點雜燴粥,灑上不知從何弄來的食鹽就這麼食用,想要享受僅有的一點吃飯樂趣。為了促進食欲,需要把味道調濃一些,這種狀況下變成營養不良加上食鹽攝取過量,許多人都因此出現浮腫症狀。 某次當大家列隊進行戶外勞動,通過赤塔中心街道的某餐廳前時,有人發現廚房流出的排水溝中,混著凍結的麵包屑。當時俘虜同伴為了麵包屑離開隊伍,卻遭監視士兵怒斥,謙二看到這一幕,內心倍感淒涼。 在這種狀況下,另一個痛苦的回憶便是上廁所。因為房舍內部沒有廁所,所以即便是在夜晚,也得走到戶外。從房舍門口到廁所大概距離五十公尺,那只是挖掘一條細長溝渠的露天廁所。 營養不良後變得頻尿。如果身體狀況再差些就會拉肚子。最糟的時候,還沒走到廁所就會漏出來。夜晚大家都頻繁起身去小便。就算睡覺的時候,也會有營養不良的人的尿液從木板搭組的上層臥鋪縫隙中漏下來的狀況。 自己也曾有隔不到一小時就得去廁所的經驗。兵營內有輪值站崗的人,站崗者身上拿著從大隊本部領來、未遭蘇聯軍隊掠奪的手錶,就站在壁爐旁看守。我問了輪值那個人才知道,距離自己上次去廁所還不到一小時。 在零下四十度的夜晚走出戶外,並不會感到寒冷,而是感到疼痛。不過去露天廁所即便露出屁股,因為屁股是圓的,還不至於凍傷。會遭凍傷的是突出的如鼻子或手指部分。如果鼻子凍紅了,不小心翼翼取暖回溫,鼻子就會掉下來。 堆積在廁所的排泄物立刻結凍。如果放任不管,凍結的排泄物便會堆成小山,甚至扎到屁股。之後這些凍結的排泄物就會溢到踩踏的地板上,整個地板都是凍結的大小便。半途漏出的小便也立刻凍結,體力不好的人,踩上這種結冰便會滑倒。營養不良後會出現夜盲症狀,走到暗處更容易跌倒。 上完廁所後也沒有草紙可以擦拭。大家原本以為「俄國人吃的東西不一樣,他們本來就不需要廁紙擦拭。過一陣子我們的大便也會變硬,也就不需要擦拭了。戰俘營並非特例,當時俄國人的廁所普遍都設在屋外」。話雖如此,「最初的冬天實在辛苦。拉肚子的人們,只能以手邊的衣物或破布擦拭屁股」。 在這種情況下,因營養不良與過勞,陸續造成人員死亡。「有時會發生早上大家起床時,才發現某個人死掉了的狀況。不過只有最初過世的人有葬禮,之後大家為了自己活下去就費盡心思,根本沒有餘裕去理會別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俘虜們在戰俘營迎接正月。根據《赤塔會會報》中原軍官俘虜們寫的回憶錄,他們當天早上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庭院,朝著皇居方向唱頌了三次萬歲。 可是謙二說「完全不記得這件事情」。 軍官們即便外出勞動,也只是負責監視,生活比較輕鬆,可能還有那種餘裕。不過那大概也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行為,不過是想念日本,依照著大戰前的習慣做相同的事情罷了。就像新年初次到神社參拜一樣。第二年之後,就幾乎沒有這樣的舉動了。 這個正月,謙二記憶最深刻的是前往探望營養不良的俘虜好友「京坂君」。京坂是駐紮新京第八航空通信聯隊的新兵,與謙二一樣,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東京入伍,接著直接送往滿洲。在隊上大部分都是較年長且居住於滿洲的日本人的狀況下,謙二與京坂因為年齡與境遇相近,進入戰俘營之後成為好友。 謙二本人幾乎沒有寫下任何西伯利亞時期的記錄。他唯一寫的一篇,就是對京坂的回憶。下文就是一九八○年代時,他發表於居住的新興住宅區自治會誌上的文章:〈對某位青年的追憶〉,《紫陽》第二號,一九八六年。 昭和二十年八月。我以現役新兵的身分,待在滿洲東部牡丹江近郊之處,對蘇聯無條件投降後成為戰俘,十月下旬遭遣送至西伯利亞東部的赤塔戰俘營。 正如大家經常看到拘留猶太人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照片一般,大約五百人如沙丁魚一般擁擠,睡在三層的通鋪上。 對於未知的未來充滿了精神上的不安。不僅得負擔重度勞動,而且食糧不足,讓大家幾乎處於饑饉狀態。一天比一天冷的空氣,預告著即將到來的酷寒,簡言之,那是一種接近恐怖感的寒冷程度。望鄉、飢餓、寒冷。僅靠著或許某天仍可回家吧,這樣的期望支撐著自己的生命,活過每一天。 十一月下旬,已經出現了好幾位死者,而且有幾十個人也奄奄一息。與我同梯的京坂君也開始出現營養不良的症狀。他開始患有夜盲,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著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地時,他必須牽著我的手前進。不這麼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麼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於開始出現失禁症狀,上頭免除了他的勞動,讓他進入醫務室修養。雖說如此,自然沒有任何醫療處置,只是放任他休息睡覺而已。 新的一年來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這天蘇聯也休假,當天午後我前往探病。病房中排列了七、八張病床,壁爐中燃燒著稀少的煤炭,根本提昇不了溫度。溢出的水在地板上結凍,三層玻璃窗除了中央部分,全都結了一層厚冰。我從窗戶向外望,看到了俄國人的親子走在路上,家家戶戶的煙囪冒出炊煙。現在我處在一個遙遠的世界,這裡沒有所謂家庭這種東西。 看他衰弱的程度,任誰都知道大概來日無多,我與他說了什麼話,幾乎都忘記了。當時也沒有任何好消息可說,無非就是說些老套的安慰話語罷了。 可是他卻雙眼看著不知名的遠方喃喃自語,說出「現在,日本內地也在過正月吧」、「好想吃麻糬啊」這兩句話,至今仍然殘留在我記憶的片隅當中。 幾天後他過世了。我自己也因為連日的重度勞動,加上寒冷與四、五天的下痢,變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幾日什麼時候死的?過世時大概是什麼狀況?我究竟問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記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度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方式。 如這段文章所寫一般,此時謙二也因營養不良,開始出現下痢症狀。一月開始的發電所壕溝挖渠作業中,也發生過拉在褲子裡,直接穿著髒褲子回到戰俘營的狀況。至於弄髒的內褲,便靠著火力發電所排水溝的溫水勉強洗淨。 到了二月,下痢狀況愈形嚴重,在蘇聯軍醫的判斷下,免除了戶外勞動作業。但還沒到必須入院的程度,所以讓他留在戰俘營兵舍內休養。同樣留在兵舍的俘虜夥伴,勸誘他一起在營舍內翻找食糧。外出作業的俘虜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給的黑麵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謙二受不了引誘,也加入他們,找出這類食物吃掉,但卻留下很深的罪惡感。 如果是偷蘇聯的食物或物資,完全不會有什麼好猶豫,但對同樣餓著肚子的俘虜,拿走他們珍藏的麵包,自己卻感到非常後悔。根本不該這麼做的,因為寒冷、飢餓與健康狀況不佳,自己連正常的感性都失去了。 免除戶外勞動僅是暫時性的措施,沒多久謙二又被趕出兵舍,繼續執行溝渠挖掘作業。 如果繼續保持這種狀態,謙二很可能會步上與京坂同樣的命運。 不過這時候,謙二的幸運派上用場了。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很快就開始改善體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蘇軍的亞夫馬德林上級中尉開始擔任第三任的戰俘營管理長官。謙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長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長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務。恐怕是因為物資盜賣事發,上級察覺管理體制不完善,所以才出現人事調動。俘虜同伴間有人看到前任所長銬上手銬被帶走的情況。亞夫馬德林透過通譯對俘虜們發表訓示,表明將改善至今為止的違法情狀。確實,在那之後食糧分配的狀況獲得好轉,當時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短暫時期還提供超過規定的糧食量。 我自己能夠活下來,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進入了混合編成的部隊,在戰俘營當中較沒有階級差異;另一個就是戰俘營體制很快地得到改善。我待的戰俘營位於蘇方軍團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鎮內,因此很快地獲得改善。遠離城鎮散布各地的戰俘營應該會出現更多的死者吧。 謙二認為自己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這些客觀條件在偶然之間湊齊的關係。他自己並不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的判斷力好或者足夠「用心」、擁有驚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因素,才能活下來。 我認為死於這個時期的人們,並沒有什麼特徵或傾向。例如精神上較衰弱、入伍前從事什麼工作等,我不認為是這些條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畢竟軍官們無須勞動,因此士兵這邊死者較多,這是擺明了的事實,任誰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據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手記,有許多人描述,記得年輕時太過無所事事引發了焦躁感、或者因為自己悲慘的命運而幾乎發狂等回憶,但謙二卻如此表示:「我沒想過這些事情。光是要活著就耗盡心力了。那種抽象性的思考,應該是原本就屬於更高層級的人,或者無須戶外重度勞動的軍官們才會有的想法吧。」 不只西伯利亞拘留經驗,關於戰爭體驗的記錄,不管是學徒兵、預備軍官、高階軍官等等,大多是擁有學歷與地位優勢的人所撰寫的。這些記錄自然是貴重的文獻,但同時也是站在特定立場寫下的。生活缺乏餘裕,識字能力低落的庶民,並沒有留下自己描述的歷史記錄。 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虜人數,相較之下非常少。根據大戰之後由俘虜們組成的同友會雜誌《赤塔會會報》所載,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該所死亡人數「約四十五名」。謙二回憶道「記憶中應該更少一些」,不過四十五名死者,大約占收容人數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亞的拘留戰俘大約有六十四萬人。其中死亡人數大約六萬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謙二的戰俘營不見得如他所說擁有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隨著冬季過去,發電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虜們的作業改為整理擄獲物資或幫忙蘇聯軍官家庭進行排水整理等較為輕鬆的工作。戰俘營的待遇也逐漸獲得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戰俘營兵舍也透過俘虜們的勞力獲得增設。三層臥鋪改為兩層,居住環境較為改善。不過,同時期也開始設置三重鐵絲網、配有探照燈的衛兵樓等設施,警戒變得更加嚴密,但至少此後這個戰俘營再也沒出現過死者。 當大家精神上開始多少有些餘裕後,關於可以歸國的希望性觀測、謠言,便開始四處流竄。戶外作業時看到載著俘虜的卡車,完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就說那會不會是移送日本人歸國的車輛?類似這種穿鑿附會的傳言,不斷在戰俘間擴散。可是,距離謙二實際回到日本,仍需要兩年以上的時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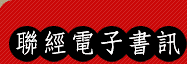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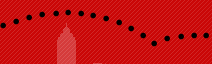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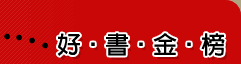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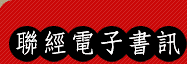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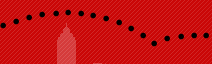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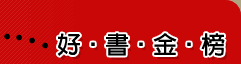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