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國文課:比國文課本多懂一點的文學講堂
一脈語言
能衍流多少風貌各異的文學書寫?
一份課本
能包藏多少在場與不在場的想像?
雲集60位以上作家、學者、評論人、研究者、現場教師與學生
針對國文課本的各面向與議題抒發塊壘,一咏胸臆,有話直說
大膽直剖、透視,完全解讀國文課! 【內文選摘】
再桃源
陶淵明〈桃花源記〉
陳建男╲文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將同時期諸多民間傳說、志怪故事,透過藝術加工手法,點綴成文,這樣的書寫對愛讀《山海經》、涉獵志怪的陶淵明,大概是牛刀小試吧。 漁人無心而至,刻意留跡而迷失其路,陶淵明大概也沒有想到,自己有意為之,反而成為後世美好想像、理想世界的開端。「桃源」歷唐宋而逐漸成為創作重要的主題,在詩詞中或為寄託,或為求證,或為翻案;在繪畫中,《桃源圖》或為寫意,或為寫實;在新詩中,無論是羅智成〈桃花源〉系列詩作對文明的省思,或楊書軒對蘭陽地區由於經濟開發而失落的感嘆,都可見「桃源」成為文學脈絡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中學課本裡的陶淵明,無論是〈五柳先生傳〉還是〈飲酒〉,多半強調任真自得的一面,然而在〈桃花源記〉之外,我總想像喝得醉醺醺的他在醉眼間所看見的不正經世界,也許光怪陸離,卻親切可愛,一如偽署陶淵明所著的《搜神後記》。或許在他腦中有一個類似《山海經》的世界觀,就像《歐赫貝奇幻地誌學》一樣,桃花源不過是他準備勾勒的一處地景。 而在簡短的〈桃花源記〉中,我無從得知此處的人是真的天性純樸,還是猶如電影《記憶傳承人:極樂謊言》將情感消弭,使再無嫉妒、競爭之心;是真的安居樂業,還是猶如許多反烏托邦作品中看似平等、富庶的假象。是我太過敏感還是早已不復忘機而至的赤子之心,面對簡短的文字猶存成人間的機關算計,然而中學時期的我,是曾經多麼嚮往有一處這樣自得的地方,可以不受拘束。 於是,再次回到〈桃花源記〉與〈桃花源詩〉,我想,若其中的人「一朝敞神界」,得以表達心聲,他們會怎麼說呢?是像《追逐繁星的孩子》中雅戈泰的人所言,由於太了悟生死所以只能走向滅亡?或是因害怕受侵略只好封閉入口?還是那裡有結界,如《消失的地平線》那樣踏出就老死?我總如此思量著,像蘇軾一樣,試圖解釋種種跡象,而生活在桃源的人也許早已超越這些問題,不得而知。 終究,桃源依然是永恆思辨與想像之地,就像保羅• 安德魯(Paul Andreu)所言「我經常可以感到一種不屬於醒來的時間的那種平靜與安詳」,或是相反。我仍嚮往有那麼一處地方,平行於這個世界,偶爾心之所至,那或許也是陶淵明常常穿越之處吧! 陳建男
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曾與甘炤文合編《台灣七年級散文金典》。 曾經的曾經
〈第九味〉 徐國能╲文 夏日的時光看似漫長,實則短促,在窗邊偶然凝視綠岑岑的樹上飛鳥來回、偶然辨認不知何處傳來隱約的悠悠琴韻、偶然在燠熱的風裡沉浸在回憶中,連書頁都還沒有翻過,茶便緩緩涼去,一個上午也就沉落在細瑣的思緒中而終於無聲消逝了。我並不驚訝時光的飛逝,只是感嘆事業之無成。年華耽美,好夢不驚,世界自有安頓每一個渺小人類的法則,我們蜷曲在這無可置辯的歡喜悲哀,然後老去,像枯黃的落葉始終懷念新綠,像一則漫長的故事之尾,忽然有意追索那很久很久以前的開始。 我時常被迫想起往日,那個惶惶終日而無可安居的自己。 我從小就接收到一種資訊:寫作。 寫作是一件很偉大的,真正值得去做的事;在我的家庭中稱之為「文筆」,生活四周一直存在著這種氣氛或暗示:在漫長的一生裡,當你閱讀、遊歷、成功或者失敗,其根本都是在為某一次的寫作做準備,彷彿一定要寫一點甚麼出來,否則人生就是白活;或者反過來說,即使你一無所有,但是你能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些甚麼,能感動或啟發任何一個人,如此人生便不再徒然。我不知道這樣的觀念是怎麼來的,但它就是存在我的周邊。在資源相當匱缺的年代,家裡最多的東西就是書,而成長中花了最多的時間做的事,就是看書。「鍛鍊文筆」貫穿所有生活,元宵要猜燈謎、中秋要背唐詩,旅遊遇到寺廟必定要看看他的楹聯,那些書畫展覽上寫的字句回家後必然有一番討論,我甚至還收集了一套唐詩宋詞元曲的郵票,這一切,都是為了培養寫作而產生的活動,我的父母對於寫作一事的崇慕,我現在想來幾乎近於宗教。 雖然我也做了一些努力,例如拿個小本子抄錄一些偶然見到的詩詞或對聯,把握機會就背下一些成語故事,但我的作文成績始終很糟糕,父親為此擔憂,不僅狠心買了一大套中央日報集結報上方塊文章的小冊子,要小學的我好好學習裡面忠黨愛國的文筆;後來還添購了某老師出版的作文指導,裡面包含了學生的作品和老師嚴厲的批改,可惜這些我都沒有學會,至今唯一記得的是最後一篇類似小說的作品:一個女學生和國文老師戀愛,去烏來喝了高粱酒而終於失身的故事,那故事我反覆一讀再讀而成為夢魘,日後看到國文老師或是高粱酒,都會讓我想到她—那個終於明白自己被騙卻無言以對的嬌怯女生。 中學以後我的寫作更是糟糕,完全不得要領,高中聯考作文有八十分,是兵家必爭之地。我們的導師就是國文老師,她發明了一種奇特的寫作法,班上有一位同學,無論寫甚麼題目都套用那固定的幾句話,老師非常讚許他的機智,要大家學一學。這套辦法目前在補教界相當流行,就是背幾段範文套用在所有題目上,這不僅教壞作文,連人品也教壞了,實在可嘆。惟我那時愛上現代詩,我偏要寫些似通不通的句子在作文裡,「文不對題」、「不知所云」是我最常遇到的評語。某日《北市青年》刊登了我的現代詩作,同學老師傳來傳去都說看不懂我在寫甚麼,最後,老師叫我去面談,很認真地勸我不要浪費時間再去寫這些風花雪月的東西,要好好上進做人。可惜我當時愚魯,不聽教誨,聯考落榜後只好去念辭修高中,卻不知冥冥之中卻開啟了我一生契機。 我第一次獲得文學獎就在高一,校刊社辦了一個「金穗獎」,我得到新詩第一名,備受稱譽,我這才明白寫作與成名這件事原來有關,爾後數年我便一直追逐著獎項,被聲名與獎金所誘惑,而幾乎忘了自己為何要寫作,又到底要寫些甚麼。尤其有了一些經驗,大致可以在題材、技巧上取悅評審,怎麼寫容易得獎漸成一種會心,恍然「文筆」之意原來如此。 但有一日我卻感到茫然,那時我碩士畢業了,在博士班研讀古典文學,重新閱讀在過去只感其文字之趣的作品,我深深發現其藝術的輝光來自於心靈苦旅而結晶出的蒼涼悲憫、慷慨寂寥,即便是宴會酬酢的短詩、贈別即興的樂章,也有一種我永遠不能觸及的覺悟與深情,於是我想毀棄我過去所有的作品及寫作意識,世間何必多我一篇贅詞來汙染文化呢? 可我受到薰習太深,生活中微小的舉動、偶然的言語,都逼使我往寫作之路聯想與發展,寫或不寫當時都是非常煩惱的。有一天回憶起了童年的點點滴滴,忽然想起父母從小對我文筆的鍛鍊,我想寫一件成長小事來回報他們一生的付出,證明他們的努力並不虛無,同時也作為我寫作的結束。 現在我去中學演講,經常被問起兩個問題:一、文章中為何如此老成?二、「第九味」是什麼? 我想我這裡的絮語就是勉強回答這兩個無可回答的問題。 我曾經是一個做過文學夢的孩子,我想抄錄一段經典文獻,作為我這篇囈語的結束:「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徐國能
一九七三年生於台北市,東海大學畢業,台灣師大文學博士,現任職於台灣師大國文系。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台灣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等。著有散文集《第九味》、《煮字為藥》、《綠櫻桃》、《詩人不在,去抽菸了》、《寫在課本留白處》等。 語言與文字之間的繩索
朱國珍/文•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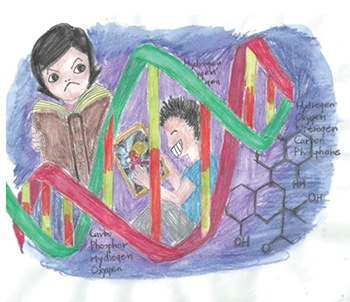
身為母親兼創作者,針對教國中生寫作文一事,我毫不謙讓自己是個「最成功的負面案例」。常常被氣到想把孩子拖去驗DNA,究竟十三年前有沒有從醫院抱錯嬰兒回家?! 學校老師重視作文,每週認真出題訓練孩子思考。關於「週末」,兒子寫道:「星期六,我根本就是擺爛人生,整天宅在家打電腦還吃了三包泡麵,因為太無聊。」老師希望孩子們想像自己的未來,珍惜光陰莫虛度,於是大膽命題「我死前那一幕」。兒子認為「這題目聽起來好不吉利喔,有點不想寫。為什麼那麼小就要給我們寫關於很久很久以後才會發生的事啊?哪有人會假設自己怎麼死的嗎?」說到「新學期新氣象」,破題如此:「新學期要開始了,但好像上一個學期剛完馬上接到下一個學期,有點坑爹啊。」 我試著向他說明起承轉合的道理,從曹丕〈典論論文〉,講到蘇東坡〈赤壁賦〉,分析論述、閱讀、思想與感受,以至提升人生境界與曠達修養的重要性。稍後他在〈我最暢銷的書籍〉,這篇文章裡作出結語:「說實在的,我想我自己本來就不是寫書的料吧。假設這本書暢銷好了,那我應該也不知道這本爛書到底怎麼暢銷的吧!」 兒子與我無話不談,我常常在他的語言裡發現超齡智慧。他十歲時我們聊到傳家之寶,我說:「媽媽沒有珠寶傳給你,只有一隻心愛的鋼筆。」他說:「最好的傳家寶不是物品。」我問:「那是什麼?」他回答:「是榜樣」。主持大型活動前夕,我在家裡獨自彩排開場白與流程,看到我重複背稿的兒子,忍不住問:「妳會緊張嗎?」「會。」我肯定地回答。他說:「不要緊張,不要想太多,妳很棒!」這樣在生活中觀察入微,語言精準又溫柔的孩子,為何在使用文字時,會將一篇文章寫得離題又措詞輕率,絲毫沒有任重道遠的胸襟?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那條繩索,像是打了無數個死結,落筆成文,竟是哭笑不得。 文章,是個人文化素養的表達工具,從命題到組織、內容,處處條理,引喻有據,陳述主張清楚明確,最後讓讀者感動認同。寫作的過程就是思想訓練與養成的過程,雖不至於達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但是完整且清晰陳述意旨,是最基本的素養。然而,我最親愛的兒子,到現在還是把文字作為搞笑的工具。 我始終懷疑兒子語言與文字產生分歧的關鍵是智慧型手機。長輩贈送的國中禮物,帶領他進入電玩與圖像的世界,語言雖新奇豐富但思考簡單,文字運用越來越退化,甚至回到幼兒程度。 為了鼓勵孩子閱讀、遠離3C,家裡原本就沒電視,我每天還抱著一本書在兒子面前晃來晃去,企圖身教重於言教,卻愈來愈像孤魂漫步。為此尋求靈媒術士給予意見,神明指示:這孩子十六歲才開竅。我無奈地跟兒子說:「既然你十六歲才開竅,那麼我現在就放手不管了吧!這樣我們兩個人也開心些。」「不行!」沒想到他爽朗的回答:「妳不可以不管我,這樣我會無止盡的擺爛下去,到時就算想振作也沒機會挽救了。」 奇怪,這段話又說得擲地有聲,充分表達獨立思考能力。當時真該叫他立即提筆成文,也許就是一堂自學成功的生活作文課。 朱國珍
清大中文系畢業,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藝術碩士。長篇小說《中央社區》獲《亞洲周刊》二○一三年十大華文小說、第十三屆台北文學獎年金獎,原著劇本得到二○一三年「拍台北」電影劇本獎首獎。著有長篇小說《三天》、短篇小說集《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散文集《貓語錄》與《離奇料理》。曾任中華電視公司新聞部記者、新聞主播、節目主持人。現為廣播節目主持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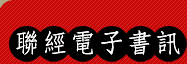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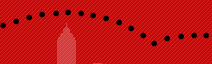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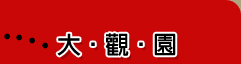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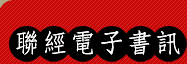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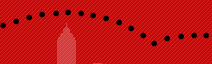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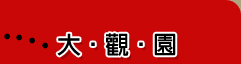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