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讓我學會的10件事
◎ 十個在父親葬禮上不該有的念頭
------------------------------------------------------
•飛機那麼重,怎麼可能飛得起來?
•爸比較喜歡大姊和二姊。
•我遺失的行李中有一袋還沒洗的內衣。
•卡爾看起來過得很好,這表示他可能有新歡了。
•醫生也會死,這肯定有點諷刺。
•我不相信神。
•棺材前面那種自動拉上簾幕的機器要多少錢?
•如果我跟卡爾說,我想……
•那牧師看起來有點像史恩•康納萊。
•我想回到父親的房子,把每瓶威士忌都拿出來排在桌上,全部喝光。
------------------------------------------------------ 內文選摘(節錄)
我想對父親說的十件事:
一,我在新加坡認識一個男人,他身上有跟你一樣的煙味和麂皮味。
二,我記得你每到假日都會戴那頂米色帽子。我討厭那頂帽子,幾乎就跟我討厭那些古蹟的斷垣殘壁一樣。
三,我希望你能說些關於母親的事,也希望你保留了一些母親的東西。
四,我十歲生日那天你送我的書,我還留著,當時我想當太空人。那本書叫做《太陽系之旅》。
五,我知道你總希望孩子之中有人跟你一樣成為醫生。
六,我常做同一個夢:我站在你家門外,屋內正在舉行派對,我聽見裡面傳出談笑聲。我按下門鈴,你卻很久才來應門。
七,偷你書房那張照片的人是我。
八,我以前會偷偷看你,看你整理庭園,或坐在扶手椅上,或坐在書桌前,背對門口。我總希望你能轉過身來,看一看我。
九,抱歉我經常不在你身邊。
十,請不要…… 父親獨自住在漢普斯特公園附近的連棟式房屋裡,那一帶的房子都又大又高傲,鋪著地磚的私人車道長而昂貴,庭院外牆高得讓人無法往內窺看。每戶都是吊窗設計,窗內掛著厚重窗簾,窗外爬著鐵線蓮和紫藤。 我在入境大廳外排隊等計程車,等的時候抽了三根菸,等到終於輪到我,低頭入車時已經因為尼古丁而頭暈作嘔。司機在車內播放莫札特的《安魂曲》,我想請她關掉,卻不知該用什麼理由,索性把雙腳伸到用來放行李的地方,將頭倚著車門,閉上雙眼。我試圖回想我背包的顏色,算是藏青色吧,有點髒。這些年來我揹著它到處跑,理當知道它是什麼顏色。背包裡裝有:牛仔褲、短褲、背心、防水外套;十包俄國香菸;一雙刺繡拖鞋,要送給蒂妲;睫毛膏和一條快用完的脣膏;一顆接近正球體的石頭,我撿來想送給卡爾,卻又咒罵自己不爭氣地流淚;一本尚未派上用場的《印度簡易指南》;一副頭燈;一張全家福,母親也在裡頭,是在我有記憶以前拍的,也是袋子裡唯一掉了我會心疼的東西。 計程車抵達得太快。我付了車錢,開門下車,踏上人行道。計程車駛離時,我有股衝動想揚起一隻手,高喊停車,說我改變心意了,我要去別的地方,隨便哪裡都好。然後坐回後座,將時間暫停,透過車窗看看倫敦。 屋子大門距街道有十一階,門階底端的兩側擺著兩棵看起來病厭厭的樹,佇立在藍色大釉盆裡。一株大月桂樹擋住了前窗,但我仍尋找著父親的身影──坐在屋前窗邊的沙發上,手上夾著一根菸,菸灰捲起。但那裡空無一人。我覺得胃痛,口中嘗到鋸木屑和睡意的味道。我從旁邊樹上摘下一片帶有黃綠色斑點的葉子,沿著葉莖撕開。 房屋大門被漆成了暗紅褐色,猶如乾了的血。兩扇豎窗周圍爬著細膩的綠色常春藤,波紋窗玻璃拒絕透露屋內的景象。 我十三歲那年,父親把我送去多實郡念書,記得第一個學期結束返家,那天父親要上班,所以蒂妲去車站接我。蒂妲的手指死命扣緊方向盤,她才剛領到的駕照就在置物箱裡。當時我站在門階頂端,看著現在眼前的那個銅製門鈴,蒂妲則四處找鑰匙。我心想,這扇門怎麼看起來不像我們家的,並伸手摁下門鈴,想聽聽門鈴聲在外頭聽起來是什麼樣子。 儘管根本沒時間,我還是從菸盒裡拿出一根菸。打火機擦過拇指。我吸得太急,咳了起來,我按住胸口,發出菸槍的淺細咳嗽聲。 ****** 十個別人可能用來描述我的詞彙:
一,遊民。
二,流浪漢。
三,街友。
四,時遇不濟。
五,野宿者。
六,無依無靠。
七,人渣。
八,邊緣人。
九,受到誤解。
十,迷失。 我是個老人,有顆躁動不安的心臟,對此我無能為力。我在這條河邊的泥濘和髒亂之間,最有家的感覺,而非在地鐵站旁那些充斥著閃耀看板和保全人員的時髦廣場上。 我四處走動。這是我所能想出最稱得上是策略的行動。我到每個地方都想像著妳。我沒有太多線索可依憑,雖然有些方向,像是髮色、身高、年齡。但我知道妳的名字。我可以喊妳,看著妳轉過來。我倆站在這裡,任憑那些單車從旁疾駛過,耳邊聽著駁船如鈴的碰撞聲,然後我們會交談。 上星期我以為自己就要死了,而我心裡想的全都是妳。當胸腔上彷彿坐了一個大人,是很難集中注意力在任何事情上的,是妳讓我撐了過來。妳總是可以幫我撐過來。 那天是在泰晤士河上游,就在國會大廈對面,在醫院旁邊有高牆的那個地方,那裡長椅的末端都刻著鳥的臉孔,坐在成堆的磚頭上可以看到河的對岸。我朝西走去,打算走到亞伯橋,在切爾西區的安靜角落找個地方過夜。那裡的警察很討厭,但如果你把自己藏好,有時他們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時我只是在路上走著。醫生說心情不好可能會導致心臟病發作,但我不確定我那天心情是否不好,至少不是特別不好。 我靠牆站立,雙掌捂著胸口,淚水盈眶像個孩子,而不是個年近六旬還能在街上求生的老人。我希望如果妳正好經過,會停下腳步,問我是否沒事。但妳沒出現,反正我早已習慣沒人注意我了。我站在那裡望著河水,心裡想著妳。有沒有可能妳已經死了,畢竟這個世界充滿危險:車禍、刀子、血栓、癌症。我繼續望著河水,想到那些可能性,我擔心自己隨時會暴斃。我崩潰了,這應該一點都不令人訝異,倒不是說我大聲吼叫或什麼的,我不是那種人──況且當任何人過的是我這種生活,都會知道低調為上。所以我沒有叫,我只是啜泣得像個嬰兒。 請別誤會,平常我不是這樣的。我喜歡喝酒談笑,喜歡躺在人行道上望著星空。我之所以崩潰只是我以為自己要心臟病發了,以為我還沒找到妳就要死了。 我也想起了她,她的名字是亮紅色的。我們出過一次遠門,去布萊頓市度週末,那次的機會很難得,一切完美。我們吃了冰淇淋和炸魚薯條。我覺得和妳說這個不太好,但我和她在一家廉價但有海景的旅館做了愛。 我說一切完美是騙人的。其實那次出遊既灰暗又陰鬱,而且我讓自己發怒了,在旅館的房間裡破口大罵,使得她雙眼緊閉,嘴唇僵硬。我想她也很不好受。 我曾墜入情網,並發現幾乎不可能從中掙脫。我發現了自己這個毛病,但人生並沒因此好過些。 我不是個喜歡看醫生的人,但經過那次泰晤士河畔事件,我逼自己去。診療室裡有新地毯那種甜膩又刺鼻的味道。我在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旁邊坐下,她站了起來並移到診間的另一頭。我試著不讓這種事往心裡去。我拿起一疊報紙,開始在上面找尋妳。一無所獲。 那位女醫生的名字有著被陽光曬暖的沙岩的顏色。她有一雙和善的眼睛,她的手碰觸我時則感覺柔軟冰涼。她說難過和恐懼是正常的,每個人初次經歷時,都覺得自己就快死了。我又哭了,就在她小小的診療室裡,診療床上鋪著紙床單。她露出微笑,遞給我一張面紙。她的觸碰和心臟病對我有同等的衝擊,也可能診間的那個女人確實傷了我,而我想她都知道。她問了醫生面對我這種人會問的所有問題,而我發現,那些問題沒一個重要的。 女醫生診斷我為「心絞痛」(agina),頭尾都是帶著冰藍色的字母a。她給我看一罐紅色的小瓶子,一種速效的舌下噴劑,告訴我那可以幫助我,不會再落得靠牆捂胸的境地。我拿了處方箋,離開診療室。接著我繼續做我做了很多年的事。我寫過妳的名字很多次,多到都數不清了。我總是在一下筆,就先寫妳的名字。 ****** 十件我所知道關於母親的事:
一,母親的名字叫茱莉安,發音像法國名字,但她並不是法國人。
二,母親很美麗。(我在父親的書房發現一張照片,裡頭是父親和母親,還有我們三姐妹。我握著母親的手,抬頭看著她。我離家求學時,把那張照片一起帶走,但父親從未提過這件事。那張照片放在我的旅行背包裡,隨著背包一起遺失了。)
三,我的頭髮顏色和她一樣。
四,父親愛她,從未找過其他女人。
五,母親做事總是不經思考。我之所以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我十四歲那年在漢普斯特公園爬上一棵樹,腳上穿的是毫無抓地力的便鞋。結果我爬得太高,摔下來跌斷了腿。前往醫院的路上,父親說:「妳和妳媽一個德性,艾莉絲。妳就不能先停個五分鐘,想想這樣做可能發生什麼事嗎?」
六,母親過世後,父親將所有和母親有關的東西裝進黑色垃圾袋,包括蒂妲和賽希非常喜歡的藍綠色和金色靠枕,放上車子載走,而且沒載回來。
七,夏天的時候,母親的臉頰和肩膀會長出雀斑,和我一樣。(這是父親告訴我的,說完還臉紅,我從未見過父親臉紅,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八,母親和父親經常吵架。(這是賽希說的;蒂妲則說她不記得了,只記得她總是跑去坐在籬笆上。)
九,母親過世時駕駛的是雪鐵龍GSA,當時她考取駕照剛滿五個月又二十一天。判決書上寫著意外死亡,那在我聽來太像偶然了。
十,如果不是為了我,母親那天根本不會開車出門。 父親的胰臟裡有癌細胞,這是賽希在電話上告訴我的,當時我站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市一家旅舍的櫃台前,她站在父親家的走廊上。長途電話充滿雜音。我連胰臟在哪裡都搞不太清楚,而我從未向賽希承認過這件事。 賽希認為我這樣下去注定完蛋。妳是在浪費妳的才能,她說,動不動就飛到地球另一端。妳是跑不過時間的,她如此說,意思是叫我早點生小孩,以免子宮枯萎。卡爾的事妳處理得很對,但妳必須思考如何安頓下來,她對我這樣說。只有塵埃才會落定,只有沙塵才會沉澱,我對她說,況且卡爾有什麼不好?她聽了只是嘆了口氣,一如往常,讓我覺得自己只有五歲。 我捻熄香菸,摁下門鈴。幸好來開門的是蒂妲。她穿著窄管牛仔褲和寬鬆的橘色T恤,臉色蒼白疲倦。她背後的走廊鋪著黑白相間、有如棋盤的磁磚。記得小時候我們曾在走廊地上用粉筆畫格子,玩跳房子遊戲,因為腳底踩上冰涼磁磚而大笑不已。 「艾莉絲。」蒂妲張開雙臂,她身體柔軟如棉花糖。我將額頭倚在她胸前片刻,吸入她身上輕柔的夏季香水氣味。賽希從樓梯上走下來,她穿著乾淨的白色便鞋,黑色亞麻長褲,藍綠色無袖上衣,頭髮看來剛剪不久,染了紅色,頗有化學顏料的感覺。她遺傳了父親的眼睛,眼珠是庭院肥料的深褐色。而我據說遺傳了母親的眼睛。 我不會哭的。我放開蒂妲,稍微退開。賽希手上拿著一只空了的玻璃水杯,化妝下的肌膚有點紅腫。 「妳應該先打個電話來的,」蒂妲說:「我可以開車去接妳,省得坐計程車還要忍受噪音。」 「沒關係。」我說。三人站在走廊上,靜默不語,氣氛尷尬。我朝樓梯看了一眼。 「他在睡覺。」賽希說。我心中燃起一把十分熟悉的怒火。我們三人站得太近了。走廊並不窄,但我覺得呼吸困難。 「旅途還順利嗎?」蒂妲問道。「我查過了,一共要飛四千三百哩,是不是很驚人?」 蒙古最令我醉心的莫過於那裡的地平線,那廣闊我從所未見,無盡的大地,無垠的天空。我將門關上,卻忘了那扇門會卡住。 「妳得要……」賽希說。 「我知道。」我將門拉過,向上提起門把,再用力關上。 賽希看了看我的黑色小背包,又看了看我的背後。「妳的行李只有這樣?」 我的腦海浮現行李大廳的情景:日光燈,一排排推車,嘎嘎作響的黑色橡膠輸送帶。我站在轉盤前,等著我的大背包出現,眼看著人們各自從輸送帶上拿起行李,匆匆離去。直到轉盤上剩下四件行李不停循環,兩個黑色硬殼行李箱、一個用報紙和膠帶包起來的長型包裹、一個提帶老舊的粉紅旅行袋。我站立原地,直到螢幕換上另一個班機編號和出發地,一群剛抵達機場的旅客聚集在我身旁,轉盤上出現新的一批行李。我想過乾脆隨便抓個行李離開好了,但我並未這樣做。 「我上樓去。」我從她們旁邊走過,盡量靠著牆壁,避免產生肢體碰觸。 「艾莉絲,他正在睡覺。」賽希將手放上我的手臂。 「我去燒水,我們可以喝杯茶。」蒂妲的手指絞著T恤下緣。 我脫離賽希的手。「我不會吵醒他的。」 我踏上四格樓梯。樓梯漆成白色,中間鋪著紅色地毯,以細銅條固定。卡爾第一次來時曾拿這樓梯開玩笑,那個週日他來這裡吃了一頓沒完沒了的冗長午餐。他說,每次我站起來去上廁所,都覺得自己像是什麼大人物。我聽了大笑,因為我從未想過會是這樣。這時我真希望卡爾站在我身邊,扶著我的手臂。我還留著他的電話號碼。有時我會怔怔坐著,盯著那些數字。 「艾莉絲,」是蒂妲的聲音,她蹙起眉,臉皺成一團。「妳……」她的雙手絞在一起。「妳要先做好心理準備,親愛的。」 父親的房間位於二樓的屋子前側,裡頭有兩扇豎框凸窗對著街道,在紅色磚牆之上,各別正對與背對著屋子後方的庭院。我打開房門,盡量不發出聲音,走進房間。厚重綠色窗簾拉了起來,阻擋日光。沙發旁的立燈在它周圍投射出一圈暖黃色的燈光。我不想看向床鋪,因此朝衣櫃望去。衣櫃邊緣鑲著小三角圖案的木質飾板,一面橢圓形鏡子,金屬鉸鏈色澤暗沉。我抬頭看著天花板醜陋的玫瑰圖案,以及簡陋的枝型吊燈,上頭還有六根假蠟燭,佇立在積滿灰塵的支架上。 賽希曾告訴過我,在我出生之前,在還沒搬到這裡的另一棟房子裡,她和蒂妲被容許在週六早上進入父母的臥室。她們會擠進父母中間,吵著要聽故事。說完故事之後,父親若不用工作,就會起身下床,在藍色睡衣外加上睡袍,走下樓去。蒂妲和賽希會在父親留下的溫暖床鋪上滾來滾去,等待樓梯上再度傳來父親的腳步聲和托盤的喀噠聲。而這週六的晨間故事和共進早餐時光,在搬來這裡與我出生之後,就再也沒有了。我問賽希為什麼?她只是噘起嘴,聳了聳肩,彷彿這怎麼說都是我的錯。 房間裡瀰漫著皮膚、汗水的氣味,而且很熱。我將手放上沙發椅背,側耳凝聽,聽見水管發出的輕微滴答聲,鳥兒在窗台上對同伴啁啾細語,以及父親的呼吸聲。 我上次見到父親是在我飛往莫斯科前幾天,我們在南格林區一家新開的西班牙餐廳吃晚餐。西班牙式前菜,一瓶香醇紅酒。不景氣要來了,艾莉絲,父親說,我不確定這是個離職的好時機。反正我只是個臨時雇員,我說,而且我有些存款。我需要離開這裡。妳總是需要離開這裡,父親說,為什麼會這樣?我向父親說了和卡爾分手的事,但這解釋不了其他幾次的遠行。我試圖回想當時父親看起來是否蒼白或削瘦,是否有生病或擔憂的跡象,但卻想不起來。 躺在床上的男人看起來不像父親。 父親有堅毅臉孔、方正下巴、濃密眉毛。他體形高大,雖然不胖,但身材魁梧。他肩膀厚實,胸膛寬闊。他擁抱你時──那種時候不多,但也並非沒有──你可以感覺到他雙臂充滿力量。現在床上躺的這個男人如此瘦小,怎麼會是父親。 床鋪右邊的地上放著一個藍白相間的長型盒子,一條細管從裡頭伸出,通到床上男人蓋著的被子底下。另有一根管子接到醫院常見的那種塑料袋,裡頭的黃色液體半滿。 床上這個男人的呼吸聲聽起來像老人,他臉面枯瘦,肌膚貼著頭骨,我完全認不出那張臉。床鋪左方有一張椅子,應該是從樓下餐廳搬上來的,條狀高椅背、窄椅墊,擺在這裡十分突兀。餐廳看起來一定也不協調,一個人座位被拿掉了。 我在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椅子咯吱大響。我屏住氣息,他沒醒過來。我想握他的手,但他的手蓋在被子底下。於是我坐著盯著自己的手指,上面銀戒指一只套過一只,指甲旁被咬得嫩肉可見。 「我剛到,」我輕聲說,聲音有點不穩。「我剛從蒙古回來。」我突然感到一陣疲憊。「我甚至不確定今天幾號。」我笑了出來,但聽起來不太合宜,便收起笑意。「我盡快趕回來了,我的手機有一個多星期收不到訊號,可能不只。」他的頭髮散落在枕頭上,嘴唇乾裂。我的胸腔能感覺得到他淺薄的吸呼。我想哭。我想躺在地上,閉上眼睛。我想逃跑。 「我一聽見留言就趕回來了。」 我想起在蒙古坐在吉普車後方,同車還有一對瑞典情侶及一個巴基斯坦人。當時我把手機忘在大背包裡,反正也沒有收訊。吉普車開在那條稱不上是路的路上,將我們甩過來盪過去,而舉目所及──什麼都沒有,一哩又一哩的無垠無盡,那便是此行的意義。 「這裡好陰暗,爸,你不覺得嗎?」我站了起來,把窗簾拉開。外頭下雨了,窗玻璃的外側爬滿一道道水痕。「看來又會是個很棒的英國夏天。」我說。 「艾莉絲?」 我轉過身。「爸?」我站在原地,手還拉著窗簾。我不該拉開窗簾的,光線照亮了他的臉部輪廓,在肌膚凹陷之處投下陰影。他的皮膚顏色不對勁,太黃了。「爸,你覺得……」 「很糟。」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感冒,嘶啞有痰。 「我的手機收不到訊號,」我說。父親咳了起來,臉部因為痛苦而皺在一起。 「我該什麼做?你需要什麼?」 父親將頭轉到左邊。 「這個嗎?」我走到床邊桌前,拿起一支頂端有粉紅色塊狀海綿的木籤。 「沾一些……玻璃杯裡的東西。」 玻璃杯裡裝著少許粉紅色液體,我把海綿浸入玻璃杯,遞給父親。父親將海綿輕輕拍在嘴唇上。我看得見他黃色肌膚下的每一根骨頭。也許我們在學校裡學過什麼是胰臟,我想它應該是深紫紅色的,一邊呈錐形,但我不記得它的功能是什麼。 「抱歉……打擾了……妳的假期。」父親每說幾個字就淺薄地吸幾口氣,嘎嘎作響。粉紅海綿木籤掉到床單上,弄出了幾塊漬。我把它撿起來放回邊桌。 「你沒有……」我阻止自己再說什麼。我往餐椅一坐,雙腳交疊。我不知道手該放哪,索性壓在大腿底下,手上那些戒指的邊緣嵌進我的大腿。「你知道在蒙古沒有人擁有土地嗎?那裡連圍牆都見不到。」 「那個男人……和妳一起去嗎?」 「你是說卡爾?」 「那個印度……小子。」 「他是英國人,我和你說過了,爸。我們分手了,這也說過了。」我站起走到窗前,把頭倚上窗玻璃,肌膚感覺冰涼。我想像和卡爾坐在圓頂帳篷外,看著太陽將大地染成橘紅色。「那裡還有老鷹,很大的老鷹,路邊就看得到,如果有路的話。牠們的爪子好大,光是把老鼠抓起來,老鼠就一命嗚呼了。」 我聽見父親移動的聲音,便轉過身來。他直視著我,眼白是深黃色的。 「妳知道……我愛……妳,」他說:「和別人……一樣愛妳。」 我握住窗簾,緊緊捏著拳頭。我的胃彷彿有個鉛塊,甚至比我的胃還大。我不會哭。我聽見他的喉嚨發出粗嘎的呼吸聲。水管停止滴水了。 「這很重要。我總是……對妳母親說……這很重要。」 「什麼意思?」 「讓妳……知道……讓妳知道……這件事。」 小時候父親每週五都會去桑頓巧克力店買薄荷鼠給我吃。不知為何,這時我突然想起這件事:塑膠包裝紙的噼啪聲,咬下老鼠鼻子的快樂心情,裡頭包著黑巧克力和甜甜的綠薄荷。 我們都沒再說什麼。我看見他眼皮跳動,然後閉了起來,呼吸變成細微鼾聲。我走到床邊,低頭看著他。 「拜託不要,」我低聲說:「拜託不要。」 門上傳來敲門聲,我想敲門的可能是蒂妲或賽希,進來的卻是護士,矮矮胖胖,身著藍褲子和寬鬆的藍襯衫。 「妳是艾莉絲吧,丹納先生經常提起妳。」 「是嗎?」 她繞過我。「又睡著了,」她說:「來換掉這個好嗎?」我往後站離床鋪,看著她拎起那個塑料尿袋,拉起床單。「今天窗簾拉開了,丹納先生,這樣很好,對不對?有點光線。而且妳女兒來了,這是特別的日子。」 「他說什麼?」我問道。 「他睡著了,親愛的。」但護士並未壓低聲音。透過單薄的棉質睡衣,我看得見底下父親的身體。 「我是說他提到我什麼?」 護士轉動塑料尿袋上的開關,把塑膠袋抽離管子。我看著黃色液體濺了出來。 「我得……」我朝房門的方向比了比。 護士頭也不抬。「當然,親愛的。總之很高興妳來了,他一直期待看到妳。」 我關上身後的房門。走道和過去一樣,有著亮光劑和一絲濕灰泥的氣味。我爬上樓梯,朝閣樓走去,但蒂妲把我攔了下來。 「妳見過瑪格麗特了?」她問道。 「妳說護士小姐?」 「她做得很好。」 「對。」 「賽希又泡了一些茶。」 以前卡爾都稱呼蒂妲和賽希為「條款與法則。」條款與法則最近好嗎?他見我從家族聚會回來,總會這樣問。焦慮又不講道理,我會這樣回答。我們每次都會大笑。 「我很想……」我朝通往閣樓的樓梯比了比。 「哦,艾莉絲。」她擁抱我。我的雙手緊緊貼著身側。 「他懂的,對不對?他知道我的手機收不到訊號,對不對,蒂妲?他不會以為……」我遠離她幾步,望著前方的木屑混泥牆,牆面又髒又舊。「我只是不希望他以為……」 「我做了餅乾,」蒂妲說:「燕麥餅乾。」父親最愛吃燕麥餅乾。我想像他躺在床上,聽著蒂妲在廚房的聲音,烘焙的香味傳上樓梯,飄入房間。 「請帶路,船長。」我舉起手做個敬禮姿勢。蒂妲給我一個微弱的笑,轉過身,走在我前面下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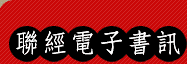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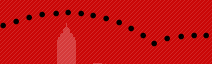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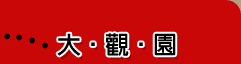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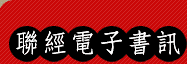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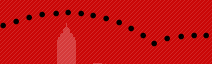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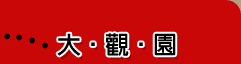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