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全球獨家一刀未剪中文版
最具權威性毛澤東傳記! ※ 本書特色:
•透過蘇聯解密檔案,獨家解讀毛澤東與史達林、赫魯雪夫的往來交惡秘辛,描繪蘇聯扶植、操控、牽制中共的錯綜關係,了解毛澤東於蘇聯羽翼下之危局和機運。 •唯一跳脫中共官方神話與個人經驗之侷限,以最新史料揭露毛澤東多樣面貌真相的權威傳記。更以過去未見的機密檔案解開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背後的真相。 •描繪這位自詡詩人的專制者如何從年輕時對革命的理想與堅持,轉變為晚年對權力的執著與狂熱。分析毛澤東嚴密矯飾、「喪事當做喜事辦」的宣傳手法,揭露毛澤東以「創造階級敵人」邁向成功之冷酷哲學和陰狠果決的鬥爭手段。 緒論/神話與事實(節錄)
歷史人物應該有客觀的傳記。可是,即使在最佳狀況下要寫出這樣一本傳記,挑戰也很大。傳記作家必須探索似乎沒完沒了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資料來源(經常涉及多種語文)、翻遍無數檔案的內容、篩析真相事實和謠言虛假、在公開角色與私下角色之間找出平衡,判斷傳主一生的智愚。傳主若是死守秘密的封閉社會領導人,困難度更要加倍。要為現代中國的創建人毛澤東寫傳,尤其如此。但是,現在距他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已經三十五載,中國已發表重要的新文件,我們又可獨家取得前蘇聯的重要檔案,因此對於現代史上這位最重要的中國領導人已經可以得出更清晰、更精細、更完整的圖像。這是這本傳記的目標。 其實,自從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國新聞記者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首度寫下毛澤東的生平故事以來,毛澤東已是無數西方文字寫作的傳記之主角。一年之後,史諾以這篇故事為中心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這本影響歷史深遠的書迄今仍在印行。從西方文字寫作的毛澤東傳記脈絡而言—我們寫的這本傳記很顯然不合這個脈絡—很值得說明為什麼這個游擊隊頭目轉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和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會面。 史諾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已是知名的新聞記者,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極端同情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的文章散見於《紐約前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等主流媒體,享有思想獨立的聲譽,並不像在中國的其他左翼記者那樣公開誇耀他們的親共觀點。 也正由於這份聲譽,吸引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注意。他們打算利用這個三十一歲的美國人改善他們的公共形象、擴張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史諾也有他本身的理由要找毛澤東。他是個雄心勃勃的記者,有追求重大新聞的本能,當然不放過可以轟動四方的獨家報導的機會。兩個人都想利用對方。史諾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抵達陝北的保安,兩天前毛澤東才在這個邊區荒城紮營。毛澤東正在躲避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委員長的追剿,國軍已經痛擊中國紅軍。 毛澤東同意接受史諾一系列訪談;訪談中,他首先詳細敘述童年身世及青少年時期的故事,然後才暢述他作為共產黨革命家的事業。共產黨挑選史諾是個很聰明的決定。這個容易受感動的美國人把毛澤東看成明智的聖哲之君、相貌像林肯、聰明、和氣、有自信。兩人一連多日在窯洞裡秉燭夜談,史諾拚命在筆記本上記下毛澤東的獨白,很快就成為毛澤東的記錄員、而不是有判斷力的記者。任務一完成,史諾帶著寶貴的筆記回北平,開始整理文稿,寫成《紅星照耀中國》。 果如毛澤東和史諾所希望,《紅星照耀中國》大為轟動,西方國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左翼人士尤其喜歡它。它把毛澤東細膩地描繪成羅曼蒂克的革命家,在已經對日益專制、一板正經的蔣介石失去信心的西方讀者心目中,觸動同情的神經。史諾這本開路先鋒作品替日後許多同樣或甚至更同情毛澤東的作者所寫的傳記定了調。日後的著作和史諾的書只有一個重點完全不同。史諾認為毛澤東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忠實的信徒,其餘作家則認為早在一九三○年代末期,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已變得威權專制且自力更生。根據這一派觀點,毛澤東身為獨立自主的思想家和主角,基本上已和莫斯科保持距離,不像在黨內鬥爭中敗給他的那些死守教條的中國史達林派。毛澤東有骨氣,是真正的中國革命家,不是史達林(J. Stalin)的跟班。這正是想向美國讀者解釋中國革命的作者,覺得毛澤東有魅力的特徵。 早在一九四○年代末期、一九五○年代初期,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布蘭德(Conrad Brandt)和諾斯(Robert North)等美國中國事務專家,就舉毛澤東和史達林的關係、以及他對中國的觀點為例,提出他自有一套「獨立」見解的說法。這套說法日後成為經典之論。他們寫說,史達林不信任毛澤東,認為他是「農民民族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甚且,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農村革命情勢上漲,正足以證明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具有「歷史角色」的觀點,乃是錯誤的。中國的「農民革命」乃是後殖民世界全面農民革命這個戲劇化時代的序幕。蘇共和中共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分裂之後,俄國和中國學者也接受同樣的思路。 同時,毛澤東也搖身一變,從腳踏實地的革命家變成一九六○年代某位傳記作家筆下的「藍螞蟻的皇帝」(指的是中國人全都穿藍色衣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毛澤東遷入從前皇室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往後幾年,除了親近同事和隨從人員,別人愈來愈不容易接觸到他。每次公開露面,事先必經仔細規劃;接受訪問和公開講話也愈來愈深奧難解。毛澤東在世時出版的西方語文傳記,包括著名的中國事務學者施蘭姆(Stuart R. Schram)一九六七年推出的最佳巨作在內,大體上依據的都是中國共產黨已發表的文件;毛澤東發表的文章、講詞和聲明;和毛澤東晤談過的外國訪客之印象;少數政治上的熟人和敵人的回憶錄;以及各種零散的資料。毛澤東具有獨立性、能夠有創意地把馬克思主義調適進中國的環境,一直都是中心論述。 乍看之下,這個論述頗有根據。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從來沒去過莫斯科,史達林也完全不認識他。同時,稱毛澤東是「反列寧主義」、指控他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這項滔天大罪的負面報導,不時從中共黨內外消息管道傳到莫斯科。因此,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說史達林認為毛澤東是「住窯洞的馬克思主義者」,顯然也合乎邏輯。一九五○年代末期,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譴責史達林主義之後,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回憶說,他意識到史達林不相信他。 然而,仔細檢視之後,關於毛澤東和史達林、蘇聯關係的這類定論,其實並不正確。事實上,近來出現的蘇聯和中國檔案透露,毛澤東是史達林忠實的追隨者,按捺著性子向他的主子一再表示效忠,直到史達林過世之後,才敢脫離蘇聯模式。 這一項揭露是值得徹底再評價毛澤東的許多原因之一。真相早就躺在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的秘密檔案中。直到最近,這些檔案才全部或局部公開。關於毛澤東政策、觀點和私生活有許多新揭秘,最有趣的部分包含在莫斯科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黨部檔案室有關毛澤東及其敵人、友人未出版的文件當中。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不久就開始組織這個檔案室。打從一開始,它的主要職責就不只限於蒐集與布爾什維克黨史有關的文件,也負責蒐集與國際勞工及共產主義運動史有關的文件。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後,它所有的文件資料全部移交給中央黨部檔案室。一九五○年代,共產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的檔案也都存放到那裡。最後,一九九九年六月,前共產主義青年團檔案也併入這個蒐藏。今天,這些整合起來的檔案被稱為「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稍微介紹一下這些檔案的內容,就可以知道它們是我們寫這本毛澤東傳記努力挖掘新資料的重要來源。 第一,它們是全世界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蘇聯共產黨黨史文件最大的蒐藏所。它們蒐藏大約兩百萬份書面文件、一萬二千一百零五份照片材料和一百九十五部紀錄影片,分為六百六十九個主題。檔案的核心部分是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十分豐富的文件。它們包括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卷宗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各種帳冊及財務收據;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給中國的指令;列寧、史達林、托洛茨基(L. Trotsky)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文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派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許多重要的中國革命家之相關個人資料。 有關中國共產黨人私人文件的蒐藏,特別有意思。不像其他許多檔案材料,即使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葉爾辛(B. Yeltsin)意識型態「解凍」的短暫時期,這些文件也不開放給大多數學者。它們一直鎖在檔案室的最高機密部門。即使今天民眾要借閱這些檔案也受到高度限制。只有本書作者之一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等極少數專家,才獲准借閱這些材料,而且因與館方人士及當今俄羅斯學者私交甚篤才能夠持續接觸到它們。這些管制材料包括三千三百二十八個卷檔,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王明和其他許多中共高階黨員的相關資料。 有關毛澤東的卷檔最令人歎為觀止。它包括十五卷非常獨特的文件,有他的政治報告;私人信件;毛澤東和史達林、史達林和周恩來、毛澤東和赫魯雪夫的會談速記記錄;由蘇聯醫生彙整的毛澤東病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和共產國際特務的秘密報告;有關毛澤東妻兒子女的個人資料,包括早先大家都不知道的第九個小孩在莫斯科出生的證明;由他在中共黨內政敵執筆控訴他的報告;還有許多蘇聯大使館和KGB特務從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就中國政治局勢呈報的密電。我們是首開記錄可以利用所有這些材料的毛澤東傳記作者—這些材料在重新評價毛澤東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時,乃是無價之寶。 補充這些俄羅斯及中國檔案的是近年來在中國出版的許多傳記材料、回憶錄和手冊。其中有毛澤東的秘書、情婦、親友故舊的回憶錄和日記,全都有助於我們重新解讀毛澤東的一生。同樣重要的是北京中共中央委員會持有的一批受到嚴格管制的文件,這些檔案近來因中國歷史學者的努力而為人所知。檔案內括十三冊的毛澤東手稿集,時間上溯至中共建黨之始。另外有七冊韶山的毛澤東家族年譜、毛澤東的私下談話記錄、毛澤東之前不為人知的草稿、演講稿、建議、評論、筆記及詩詞。 我們這本毛澤東傳記是根據以上所有這些獨特檔案及最新出現的文件,再加上許多熟悉毛澤東的人士之訪談錄所寫成。因此,它的資料最新。近來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著作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遭學術界批評,指它不可靠、判斷歪曲。我們設法避免這些缺陷,比其他任何傳記作者更仔細地、嚴謹地採用廣泛的資料來源,審慎評估證據,提出不受政治考量影響的堅實、有力的判斷。這種冷靜的態度使我們可以呈現出這位偉大的舵手之多樣性面貌—是革命家、也是暴君;是詩人、也是專制者;是哲學家、也是政客;既為人夫、又四處留情。我們展現出毛澤東既非聖人、也非惡魔,只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的確盡全力要為國家帶來繁榮,並爭取國際尊敬。可是他犯了不少過錯,自陷於政治和意識型態烏托邦的死巷,並且沉浸在個人崇拜之中,身邊簇擁著一堆阿諛諂媚的廷臣。 毫無疑問,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烏托邦者之一,但是他和列寧、史達林不同的是,他不僅是個政治冒險家,也是個民族革命家。他不僅推動激進的經濟、社會改革,也在原本半殖民地的中國完成民族革命,並且統一了深陷內戰的中國大陸。原本被先進的西方世界及日本所鄙視的中國及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手中爭回了世界的尊敬。可是,他的國內政策造成全國大悲劇,數千萬人斷送了性命。 我們也試圖寫出一個有血有肉、有趣的人的故事,花了相當篇幅講述毛澤東的性格、個人及家庭生活,以及他的政治和軍事領導。本書有許多摘自回憶錄和訪談錄的有趣故事,呈現毛澤東為人子、人夫、人父、朋友、情人,以及戰略家、理論家、政治家和政治鬥士的諸多面貌。我們從許多角度展現毛澤東也有七情六欲,會陷入深邃的憂鬱,也會有飛漲的激憤,是個有強大意志力和野心的人物,在他擔任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時,實際上獲得無限制的權力。我們的目標是畫出鮮活的圖像,希望能使對毛澤東和中國所知不多的讀者有興趣一讀。我們也試圖描述毛澤東所遇到的五光十色的眾多人物,以及他在中國居住、念書、工作和休憩的地方,從他出生地韶山沖到過得有如皇帝的紫禁城都會提到。我們這本書透過它最重要的領導人敘述現代中國的歷史,試圖傳遞中國的感受、氣味和感觸。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許多有關毛澤東生平的驚人的新事實,需要修正我們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以及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既有的共同認識。根據廣泛的研究,我們記載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建黨至一九五○年代初期持續依賴莫斯科財務支持。仔細注意毛澤東的一生,我們發現只有考量到它持續依賴莫斯科對它下達權威的政策指導和指令,才能理解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有關張國燾、周恩來、劉少奇、蔡和森、瞿秋白、鄧中夏、王若飛、陳雲、李立三、高崗、俞秀松及其他人的檔案材料也顯示,中共依然聽命於史達林及其副手,他們不但控制共產國際,手上也掌握著中共領導人的命運。我們從中共主要人物因為所謂的錯誤或「托派活動」被迫接受無數的、羞辱性的盤問及自我批判,可以看到這一點。甚至,還有證據顯示史達林在一九三八年考慮公審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及其他人在內的共產國際官員。如果不是他放棄這個計劃,許多中共領導人或許就成為他的槍下幽魂。不過,有些文件顯示,他謀殺了大多數中共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代表團人員(舉行時間為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 史達林沒把毛澤東列入「黑名單」。史達林本人及共產國際的確協助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崛起掌權。其實,毛澤東並不像東德的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或依附於莫斯科的其他中歐、東歐共產黨領導人,但是我們不再有懷疑,他的確忠於史達林,向史達林尋求指導與支持(我們談到毛澤東、史達林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的會談,就會透露這方面的內情。同樣有密切關係的是,我們會敘述韓戰期間毛澤東和史達林侷促不安的關係。史達林並沒有打算統一韓國,而是設法讓美國不只和北韓交戰,也和中國衝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國。史達林企圖進而在全球搧風點火掀起革命)。一直要到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去世之後,毛澤東才開始與蘇聯領導人保持距離。他覺得赫魯雪夫是不值得信任的小丑,刻意蔑視他。我們會顯示毛澤東和赫魯雪夫個人不和,是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蘇交惡已升高到一個程度,卻經常被低估。依據前蘇聯的秘密檔案,我們顯示在一九六○年代末期,中、蘇關係已緊繃到蘇聯領導人甚至開始考慮武裝介入中國事務,例如針對中國的工業重鎮發動原子攻擊或炸毀中國的原子基地。 我們也試圖呈現年邁的毛澤東於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這段期間一個鮮明、客觀的圖像。這段期間,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一九五八至六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企圖大膽依循獨特的毛式社會主義路線改造中國社會,卻造成極大規模的悲劇。這些事件全都根據新的檔案材料檢視,目的是指出其狂妄的目標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彼此之間的權力鬥爭;毛澤東因為上了年紀,對他們日益疑神疑鬼,技巧地加以操縱以遂其目的。 和傳統觀點不同的是,我們顯示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毛澤東最後的奪權鬥爭,而且是非常不幸、有許多嚴重瑕疵想達成其烏托邦理想—要在新的理想社會建立新的理想公民—的努力。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重建社會政治關係還不夠。即使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人還是有惰性、自私自利。每個人都會潛藏貪婪的自我,夢想重回資本主義。因此,如果聽任發展,即使共產黨本身也會墮落。他因此得到一個信念:若不先搗毀中國文化裡的舊傳統價值,就不可能建立共產主義。然而,他顯然低估了人性。這個誤判不僅造成文化大革命失敗,也使毛澤東主義的計劃全盤破滅。毛澤東所擬想的粗糙的威權專制共產主義制度、一個嚴厲統制的社會,隨著毛澤東本人去世也埋入地下。 總結而言,身為歷史學者,我們的職責不在責備或讚頌毛澤東。我們給自己訂的職責是,盡最大努力詳細地呈現二十世紀一位最有權有勢的政治領袖。我們希望本書有助於讀者對毛澤東、對他所生長的時代和國家、對他所創造的中國,有更深入、更正確的瞭解。 內文選摘(節錄)
第二十九章/思想大解放
一九五六年發生另一件事,大大震撼了中國和全世界。二月二十五日,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發表報告,譴責史達林搞個人崇拜。這位已故的獨裁者被控訴多項罪行。赫魯雪夫強調,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犯了嚴重錯誤,違反集體領導的原則,並且建立個人獨裁。他談起史達林在民族問題及農業政策上犯的錯誤,也談他在蘇聯國際關係上犯的錯誤。然而,他沒有提到史達林不信任毛澤東;赫魯雪夫倒是提到史達林對待狄托犯了錯誤。 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蘇共全代會。朱德、鄧小平及其他人員代表中國共產黨與會,他們將這個驚天動地的新聞回報給毛主席。毛澤東也大吃一驚。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才發賀電給蘇共二十次大會,照例歌頌已經去世的史達林。賀電提到「列寧創造、史達林養大的所向無敵的蘇聯共產黨」。朱德也極為尷尬,他在大會主席台上才宣讀賀電,全場掌聲如雷。赫魯雪夫這番話給人的印象是,他根本不管他的講話會在共產世界引起什麼回響。他甚至沒把報告書交給外國的共產黨過目。毛澤東必須靠新華社譯自《紐約時報》三月十日刊登的全文,才得知箇中內容。赫魯雪夫只顧著解決自己的問題。換句話說,在譴責史達林主義時,這位蘇聯新領導人的行徑與史達林無異,一點兒都不懷疑莫斯科所有的衛星附庸國家會照單全收克里姆林宮所講的一切。他們曾經在一九三九年接受令人難以置信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即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完全翻轉了蘇聯與希特勒德國的關係,而今他們也將接受史達林被批判。 然而,經過一番思索,毛澤東壓抑下原先不痛快的感覺。姑且不論其他,批判克里姆林宮前獨裁者使他徹底解脫。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四年到訪所開始的過程,現在達到它合邏輯的結尾。隔了一陣子,赫魯雪夫送來了官方正式消息,毛澤東注意到這個拆卸史達林神壇的蘇聯首腦並沒有百分之百的自信。他很明顯試圖爭取毛澤東的贊同。毛澤東為此甚爽;它證實了他原先對赫魯雪夫的印象;赫魯雪夫是個軟弱的夥伴。這個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在私函中告訴毛澤東,蘇共通過了有關史達林的決議之外,又提議協助中國興建五十一個軍事項目和三個科學研究機構。他也表示願意與中國合作,興建一條連接新疆烏魯木齊到中蘇邊境的鐵路。換句話說,赫魯雪夫企圖爭取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赫魯雪夫的個人代表米高揚和中方簽署了一份蘇聯援助興建五十五個新工業設施(包含製造火箭和原子武器的工廠)的協議。 這一切激烈地改變了中、蘇關係之間的力量均衡。從現在起,毛澤東不再需要仰事蘇聯,覺得必須抄襲蘇聯的經驗。如果說他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初推動類似蘇聯的史達林式集體化時,只敢要求以比蘇聯更快的步調進行,現在他完全可以摸索自己的發展路徑。他甚至可以試圖趕上、並超越蘇聯,把中國打造成最強大的工業強國。 他搞懂了赫魯雪夫的報告之後,於三月三十一日邀請回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而今回到任所的蘇聯駐北京大使尤金過來一談。尤金本人也想要見毛澤東。赫魯雪夫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要求尤金大使求見。然而,毛澤東以生病為託辭,讓尤金等了一段時候才終於答應見他。兩人談了三個小時。毛澤東精神十分亢奮,儘管話題嚴肅,他卻談笑風生。他希望給人的印象是,他的人生閱歷豐富,智慧深邃,能夠安然笑看世界風雲變色。然而,很顯然他無法坦然討論史達林這個話題。 他先開口告訴尤金,他認為已逝的導師「毫無疑問……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優秀忠誠的革命家」。據尤金的說法,毛澤東同時也說「(蘇共二十大)代表大會的文件使他印象深刻」。毛澤東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和代表大會後所造成的氣氛,也會幫助他們廣開言路……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不能先說話的」。 毛澤東很清楚他在說什麼。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歷史當中,它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幾乎無可避免地在意識型態、組織和政治上,都得依賴莫斯科。雖然毛澤東心知肚明史達林的奸詐陰狠,現在他一死,自己可以感到輕鬆,可是他無法公開批評他的「領袖和導師」。沒錯,他並不清楚史達林陰狠的全貌。例如,他並不曉得這個克里姆林宮獨裁者在一九三八年曾經計劃,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大規模政治審判。史達林在思索要鬥爭哪些人時,一度把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鄧發、吳玉章、楊尚昆、董必武,甚至一九三五年已被國民黨處決的瞿秋白,都列入黑名單。內務人民委員部調查員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郎方(Aleksandr Ivanovich Langfang)對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捕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人事部官員郭紹棠動刑,逼得他攀咬出上述這些人。我們不用懷疑,郎方不會自己主動去做這件事。 史達林打算在已經進行過的齊諾維也夫和卡門涅夫案(Zinoviev and Kamenev)、拉狄克和皮亞塔可夫案(Radek and Piatakov),以及布哈林和萊可夫案(Bukharin and Rykov)這三大案之外,再於一九三八年春末針對共產國際官員發動公審。這一次主要對象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約瑟夫•派特尼斯基。其他目標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官員貝拉•孔(Bela Kun)和威廉•柯諾寧(Wilhelm Knorin),至於上述中方人士只是配角。決定逮捕大批共產國際官員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定案。五月二十六日子夜一點鐘,季米特洛夫被請到人民委員葉佐夫辦公室;葉佐夫告訴他說:「共產國際裡潛伏了重要間諜。」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初,開始動手抓人;可是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國人大部分沒被抓。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如此,但是若非史達林放棄他的計劃,很有可能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遭到他的毒手。他沒有把毛澤東列在「黑名單」上,但是又有誰真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份整肅名單呢? 毛澤東並不曉得有這麼一件胎死腹中的整肅計劃,他和尤金大使的談話,大部分集中在史達林對中國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有哪些政策錯誤。他提到他和史達林歷年交往過程遭遇到哪些羞辱。最後,他告訴尤金,《人民日報》即將發表社論談蘇聯個人崇拜的問題。 這篇社論由陳伯達執筆,經過毛澤東本人及其他幾個人(其中只有少數是政治局委員)潤飾,發表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它的標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由於它的讀者對象是廣大民眾,它並沒有對前共產主義偶像做出不平常的批評。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並不希望有任何人打起反史達林的旗幟來反對他們的獨裁專政。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承認,「我們並不打算把史達林和第三國際幹的壞事統統向群眾揭露」。現在,毛澤東也不想透露他本身尋求自己的發展路徑的計劃。史達林的功過被定為七三開,但是蘇聯還是被稱頌能夠「無私地批評……過去犯的錯誤」。 次日,毛澤東接見赫魯雪夫的私人代表米高揚時,又提到這個話題。米高揚是在四月六日來中國訪問兩天。根據社論精神,毛澤東花了不少時間批評史達林對中國革命犯下的「嚴重錯誤」;可是他指出,「史達林功大於過」。米高揚在回話時,邀請毛澤東到莫斯科訪問。毛澤東問說:「去幹嘛?」米高揚不正面回答,只說:「總會有事的。」毛澤東很不爽米高揚一副家長口吻。 五月一日,天安門廣場照例舉行五一勞動節大遊行,遊行隊伍和去年一樣,高舉著史達林的巨幅人頭照。全中國各城市的遊行亦莫不如此。次日,毛澤東主動拜訪尤金。根據蘇聯外交官康士坦丁•克魯提可夫(Konstantin Krutikov)的回憶,毛澤東再次表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史達林「功過」的立場;可是他又提到上次和米高揚談話之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史達林不信任他……很顯然,史達林認為即使他最親近的副手伏洛希羅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根本比不上外國的受提攜者。」可是,他拜訪尤金另有目的。毛澤東是來表達他不同意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的一些立場。赫魯雪夫提到「兩種制度和平共處」和「現階段防止戰爭的可能性」,他不能茍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悄悄表示,它不能同意同一份報告中有關「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理論。《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有一篇文章談論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這個主張即被刻意忽視。 毛澤東決定也要對「和平共處」表達他的觀點。他採取非常迂迴的方式,不直接攻擊。他告訴尤金大使,三國時期(西元二二○年至二八○年),由於年年征戰,中國人口減少了四千萬人,而在唐玄宗時期,安祿山作亂(西元七五五年至七六三年),人口減少得更厲害。他的意思是用不著害怕和帝國主義發生核子戰爭。即使帝國主義者能佔領蘇聯的歐洲部分和中國的沿海省份,社會主義最後仍會勝利。他的結論是,帝國主義只是「紙老虎」。不知什麼原因,他很喜歡「紙老虎」這個字詞,在幾個不同場合使用過,甚至還開玩笑地稱江青為「紙老虎」。這一次,他只是迂迴地重述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與芬蘭駐中國大使卡爾—久翰•孫士敦(Carl-Johan Sundstrom)所說過的話。當時他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美國如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結果是美國和英國及其他幫兇國家的統治階級要被掃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變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他們發動戰爭愈早,他們在地球上被消滅也就愈早。 就在最近,即四月底,毛澤東在為期四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一項不尋常的講話。四月二十五日的這項講話,題目是〈論十大關係〉,它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基本上,這項講話代表毛澤東整個世界觀的重大轉折,反映中國共產黨思想正在解放的新氣氛。它界定了黨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政策,這條路將不同於蘇聯模式。首先,毛主席痛批蘇聯經驗,公開主張黨要走新路徑:「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顯然他已經開始重新檢討史達林主義模式,覺得它不夠激進,而且蘇聯的發展步調太慢。 毛澤東沒有提出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詳盡計劃;然而,他指示一些策略元素,強調需要遵循「多、快、好、省」的原則。他心中盤算的是:大幅提升對輕工業及農業的資本投資,快速開發內地省份,減少在國防部門的投資,以及加速整體經濟建設。毛澤東也談到加強對工作的精神、而非物質鼓勵,減少集中化官僚管理下的經濟範圍,並且開發相對自主的生產基地。他沒有隱瞞新策略和蘇聯策略之間的差異:「我們必須以分析、批判的眼光學習,我們不能囫圇吞棗抄襲、機械地移植……有些人從來懶得分析,只知「跟風」。今天若吹北風〔即蘇聯〕,他們就加入「北風」派……如果每句話都奉行、即使是馬克思說的話,一定大亂……我們若是已經清楚明白,我們就不能每個細節都學別人……蘇聯有許多人很自負、很傲慢。」 毛澤東的講話稿當時沒發表,一點兒也不奇怪。毛主席不只是公開批評蘇聯。他的想法與中國許多領導人的想法南轅北轍。後者包括劉少奇、周恩來c和陳雲。鄧小平也不瞭解他的想法。譬如,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主張增加人民幣二十億元的資本建設,周恩來就公開和他爭辯。周恩來認為,這樣做就會很難供應基本必需品給老百姓,會導致城市人口異常大增。毛澤東被這個主張刺痛,五月二日他把他的新主意又向最高國務會議成員提出來。 在這個情況下,中共中央覺得有必要派發毛澤東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稿,但只發給黨的高階及中階幹部。這時候,周恩來、陳雲和其他經濟專家忙著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他們沒有完全理解毛澤東的非正統想法。基本上,他們沒理睬他。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們全都忙著日常的黨、政工作,沒有時間與「偉大的理論家」進一步討論他的新構想。 毛澤東很生氣,他提的構想竟然沒人聞問。一九五六年中期,他從北京飛往廣州視察,希望能像以前一樣取得地方幹部的支持。當時天氣非常熱,廣東人飽受蚊蠅肆虐之苦。毛澤東居停的住處沒有冷氣機,可是他並不急著回北京。他必須解決一大堆問題、接見許多人、評估他們的想法、爭取他們支持他和「死硬的溫和派」繼續鬥爭。這些「溫和派」利用主席不在家,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批評「保守主義」和「急躁情緒」。毛澤東的反應卻十分孩子氣,他說:「我才不讀它。我幹嘛要讀他們罵我的文章?」 他對這些完全缺乏「勇氣與決心」,「仍有奴隸心態的殭尸」感到疲倦。不,他必須向他們展現他比全部人加起來都還有力量。
他決定要實現舊夢,游渡三江:廣州的珠江、長沙的湘江,和武漢的長江。他的確是個游泳健將,但是他的想法也的確很荒謬。這三條河流都寬得不得了,長江更有許多漩渦和急流。但是想讓他改變主意根本就是浪費時間。一九五六年五月底,他跳進水面寬逾一點五英里的、汙濁的珠江。職責在身、必須陪他下水的醫生說:「水可真髒,水色汙濁,偶爾有糞便從身旁流過。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個氣箱,全身鬆弛,兩腿微曲,彷彿睡在沙發上。他隨水流漂浮,只有時用手臂打水,或擺動兩腿。」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將近兩小時,超過六英里。不久之後,他離開廣州,前往長沙,兩次游渡一英里寬的湘江,湘江的水也沒比珠江乾淨。毛澤東高興得不得了。他大聲喧嚷:「湘江太窄,游長江去。」 毛澤東終於在六月初抵達武漢。很快地,在四十多個衛士簇擁下,他來到這條大河岸邊。當然,他沒辦法游渡長江;那會是愚蠢之舉。水流力量極大,毛澤東只是順流漂浮而下,和珠江一樣;這次漂流超過十八英里。毛澤東高興得無以言宣,新聞記者也準備好了,立刻向全國發布「我們敬愛的舵手」勇敢征服長江的「好」消息。毛澤東在武漢逗留那幾天,在長江游水三次。他後來熱切地說:「事情就怕認真對待。認真準備,事無不成。」我們曉得,他心裡念玆在玆的就是政治局裡的「溫和派」。 可是,新的一樁失望在北京等著他。政治局裡的「溫和派」正在緊鑼密鼓籌備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把個人崇拜問題放到議程上。北京的氣氛十分緊繃,毛澤東暫時不去碰黨務,躲到黃海邊安靜的度假小城北戴河避暑。他可能心裡想:「你們想逞能呀?請便。大家走著瞧!」他又玩起他鍾愛的游擊戰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夏末,他向左右宣布,基於「健康」原因,他打算交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位,只保留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一職。 劉少奇和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不希望冷落毛澤東,也趕到北戴河去。主席一直都是他們的領袖。他們只希望有些集體領導權。可是這也正是毛澤東所不能同意的。他認為,赫魯雪夫的融化不僅威脅中國,也危及整個社會主義大業,後果如何尚不可預料,中國共產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團結在他四周。 中共八大就在這兩種觀點對立衝突的背景下召開。正式會議是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開。一千零二十六位黨代表和一百零七位候補代表,代表將近一千一百七十三萬名黨員出席會議。但是,正式會議之前,從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二日還有閉門討論(所謂的預備會)。在這些討論中,敲定了大會的一切基本決策。代表們在閉門會議中討論及通過所有的決議,以及所有的基本報告和講話的文本。他們也要解決人事問題。 這一次,毛澤東非常小心。和以往一樣,為了測試他的對手,他不主持任何一次會議,也不發表任何報告。他把最活躍的角色交給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他本人要故示「謙虛」。他只發表兩次簡短談話歡迎與會代表,一次是八月三十日預備會第一次會議,另一次是九月十五日全代會開幕式。38同時,他竭盡全力推介他的構想。特別是在這兩次簡短談話,他都重申「十大關係」中的主張,他也修訂劉少奇將向全代會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的草稿。他添了下面一段文字:「中國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這一點也要弄清楚。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麼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為了明白顯示他拒絕接受蘇聯的家父長主義,毛澤東甚至拒絕出席九月十七日的會議,因為赫魯雪夫的代表米高揚被安排在會上演講。 全代會的基本調子卻完全不符毛澤東的意向。在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領導下,與會代表尊重蘇聯模式,只支持毛澤東意在加速完成史達林化的社會實驗。全代會正式宣布中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已經勝利。所有發言者都熱切稱讚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 然而,最重要的是,全代會通過的一項決議,讓毛澤東痛徹心脾。在赫魯雪夫於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的講話所創造的新氣氛影響下,中共八大的代表竟然同意從黨章中刪掉中國共產黨由毛澤東思想「指導它整個工作」這句話。取而代之的一段文字是:「中國共產黨由馬列主義指導。」鄧小平在宣讀〈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時,特別強調需要針對強欲別人接受意見、並且將它光榮化的鬥爭。他宣稱:「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固然他也提到毛澤東在反對中共黨內個人崇拜的鬥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沒有人把這句話當真。全代會恢復設置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這一點也相當重要。毛澤東親自提議由鄧小平升任總書記。即使鄧小平不瞭解「十大關係」,毛澤東認為他是「相當誠實的人」,因為鄧小平並不像劉少奇和周恩來那樣公開表示反對毛澤東的冒進。 可想而知,毛澤東並不滿意八大所通過的許多決議。個人崇拜這個問題最讓他不滿。全代會之後不久,他即決定反攻。他在接見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團時,故作不經意地說:「中國也有些人公開批評我。中國人民寬容我的缺點和錯誤。那是因為我們一直都在服務人民、為人民工作。」這些話聽來頗有向毛澤東的對手警告的意味,尤其是毛主席還解釋說,「老闆主義」在中國還不是問題。他還說:「有些人批評我之時,其他人會出來反對,指責他們對領袖不敬。」這時候,在他的親信圈子內,他開始批評赫魯雪夫的反史達林政策。他向他的譯員李越然抱怨,史達林是「該被批評、但不是殺頭呀!」他在生氣時向另一個譯員閻明復表示,赫魯雪夫「不夠成熟到可以領導那樣一個大國」。他也對其他副手說,赫魯雪夫「不遵守馬列主義」。 一九五六年發生在波蘭和匈牙利的反史達林主義事件,也大大增強了中國領導圈內的崇拜氣氛,進而增強了毛澤東的地位。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工人示威風潮下起而掌權的波蘭共產黨新領導人哥穆爾卡,將史達林派趕出波蘭工人黨政治局。其中之一即波蘭國防部長兼部長會議副主席康士坦丁•康士坦丁諾維奇•羅科索夫斯基元帥(Marshal Konstantin Konstantinovich Rokossowski)。他是由史達林欽點出任這兩項要職。原本在波蘭人民中就很強烈的反蘇氣氛,開始快速增長。同時,在匈牙利方面,由於民主革命的結果,政府權力交到頗孚民心的自由派共產黨人納吉(Imre Nagy)手中。東歐社會主義的危機,毫無疑問是因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的講話所引爆。 毛澤東對此非常瞭解,也不隱藏他對赫魯雪夫行動的不滿。十月二十日晚間,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他首次譴責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他聽到新聞報導說,赫魯雪夫打算動武、對付哥穆爾卡,他不願見到這一幕。蘇聯干預波蘭政局可能引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開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立刻召見蘇聯大使尤金。毛澤東不顧禮節,穿著睡衣,在臥室接見尤金。毛澤東十分激動地說:「我們堅決反對你們這樣做。請你馬上把我們的意見打電話告訴赫魯雪夫:如果蘇聯出兵,我們將支持波蘭反對你們。」 接到尤金報告後,赫魯雪夫驚慌不已,於十月二十一日決定,「鑒於情勢……對武裝干預〔全面〕節制。展現忍耐。」毛澤東覺得他贏了。十月二十三日半夜一點鐘,又把倒楣的尤金找到他臥室講話;當著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整個政治局核心的面,他慍怒地指出,俄國人已經完全丟棄了史達林的利劍。他說,結果是敵人撿起劍來、殺共產黨人。他說,這不啻是搬磚砸自己的腳。 現在讓毛澤東不安的大事是匈牙利的局勢。到了十月二十三日,它已經發展到更加緊張的地步。因此,匈牙利問題是赫魯雪夫和劉少奇討論的重點。劉少奇與毛澤東一直保持密切聯繫,而毛澤東起先建議赫魯雪夫,對匈牙利也採取和對波蘭相同的和平方式。他相信「匈牙利的勞動階級」能夠「重新掌控情勢,自己平息動亂」。但是情勢在十月三十日下午急轉直下。毛澤東同時接到中國駐匈牙利大使和劉少奇的報告,國家安全官員在布達佩斯被私刑處死,這下子他按捺不住了,決定不能聽任事態發展下去。看來,匈牙利的革命和哥穆爾卡的自由派共產黨改革不一樣。它有可能從根本上動搖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局勢。劉少奇通知了赫魯雪夫及蘇共中央主席團其他人員毛澤東的新觀點:「〔蘇聯〕部隊應該留在匈牙利和布達佩斯。」這是准予鎮壓匈牙利民主運動的綠燈。 十月三十一日晚間在機場為中方代表團送行時,赫魯雪夫顯然已聽進毛澤東新立場的意見,他告訴劉少奇說,蘇共中央主席團已決定「恢復匈牙利的秩序」。赫魯雪夫日後回憶說:「不再有爭論。劉少奇說,如果在北京還有人有不同意見,他會通知我們。」但是毛澤東沒有再次改變立場。結果是赫魯雪夫決定全面進擊,尤其是很快就發現,匈牙利政府宣布它有意退出華沙公約,並轉向西方國家及教宗求助。十一月四日,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匈牙利人民革命淹死在血水中。
儘管如此,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導人十分震驚,社會主義國家裡竟然會發生自由民主運動。十一月中旬,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繼續發展他的「棄刀」論。他對蘇聯的攻擊空前猛烈。他控制不住怒氣,甚至宣稱許多蘇聯領導人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丟棄列寧的刀」。甚至,他更標舉他和莫斯科在另一範圍也有歧異,他首次公開批評赫魯雪夫的「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之理論。毛澤東強調說:「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當然,他發動的論戰明顯是設計出來的:畢竟,沒有人能預測未來。縱使如此,從這時起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蘇聯和中國領導人一直激烈辯論「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毛澤東也試圖向東歐若干國家領導人招手。他認為這些國家的根本問題,在於其共產黨員沒有妥當地進行階級鬥爭。因此這些國家有「太多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
利用這個情勢,他同時試圖推動在中國加快經濟發展步調的主張,再度攻擊仍然傾向蘇聯經濟經驗的「溫和派」。他在二中全會前夕指出:「蘇共二十大有個好處,就是揭開蓋子,解放思想,使人們不再認為蘇聯所做的一切都是絕對真理,不可改變,一定要照辦。我們要自己開動腦筋,解決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 毛澤東一方面確認社會主義已經勝利;另一方面,他表示懷疑黨有能力在劃時代的短時間內,把中國改造成為軍事與經濟大國。為了重振黨的活力,他籲請非黨員群眾,尤其是「民主黨派」及其他知識分子,來批評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黨員,對黨的政策提供大膽、誠實的評價。他呼籲直接針對官僚主義發起大規模的意識型態運動。他或許希望能把來自底下的批評,導向他在黨內領導圈的對手。他提議這項運動的口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毛澤東最早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這個口號,但是當時由於黨內的反對和知識分子的懷疑,並未形成風潮。現在毛澤東再次試圖發動運動。雖然他的講話一直要到六月才發表,中共中央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通過措施以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把他的指示作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之基礎。這項決議成為重振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毛澤東認為黨已經變得太保守、太官僚化,因此才不能採納他激進的政治、經濟原則。黨內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成為密集批評的目標。 五月間,新的「百花運動」正式展開。毛澤東顯然賦與人民完全的言論自由。他現在的講話鼓勵意識型態和政治的多元主義。從五月初起將近一個月時間,中國所有的報紙和其他大眾宣傳工具,統統開放,任何人想對政治議題發表批評,一律歡迎。然而,許多人批評的不是「個別錯誤」,而是整個共產黨專政的制度。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基礎—馬列主義—遭到猛烈批評。民主黨派人士章乃器、章伯鈞和羅隆基等人特別活躍。他們的反共文章獲得許多大學教員的支持。學生陷入騷亂。 中共領導人和毛澤東本人顯然沒有預料到會有如此熱切的反應。他們還沒準備好和對手認真討論,而對手顯然頗孚民心。毛澤東顯然失算了。知識分子並沒有幫他的忙,他們展現出的是排斥共產主義。除了終止運動,已經別無辦法。六月八日,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共中央通過一道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言論自由全面取消,共產黨恢復原先的政治和意識型態暴政。同一天,《人民日報》對政策突如其來大轉彎提出以下的解釋:「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 《人民日報》等於承認黨的領導人發動一場大規模政治騙局。現在,一場規模空前龐大的鎮壓運動排山倒海撲向知識分子。中共黨史上第一遭,「右派資產階級分子」的標籤貼到數百萬知識分子頭上。大約五十萬人被打入勞改營。他們並不全都批評政府,許多人其實忠於新政府,只是被陰謀及「階級鬥爭的邏輯」害了。
恐怖的氣氛使得毛澤東可以克服他在經濟建設領域的主要對手,周恩來首當其衝。一九五七年夏末,毛澤東抨擊周恩來,指責他犯了嚴重錯誤,試圖追求中國經濟平衡發展。毛主席宣稱他本人本質上是個冒險家,不怕搗亂局勢,以便加速中國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 就在三中全會中,毛澤東首次提到農業生產巨幅增長的可能性,提議重唱早已遺忘的「多」與「快」口號。他說:「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麼多時間。」 毛澤東覺得時間站在他這邊。社會主義在中國基本上已經建設起來,工業已經開發,在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共產黨專政也堅強屹立。現在看來,原本聲勢鼎盛的莫斯科,已經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它在共產世界的權威;波蘭和匈牙利的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事例。當然,赫魯雪夫握有核子武器,而且蘇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發射了斯普特尼克人造衛星。可是,毛澤東要向所有這些共產黨同志顯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現在究竟在哪裡。 毛澤東開始發展他最早在〈論十大關係〉中所提出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的思想。他前思後想各種大躍進的方法,想要找出一種善加利用中國相對優勢、尤其是取之不竭的人力資源,以加速經濟發展的新模式。他歎息說:「我們這個國家就是鋼太少了。就是要搞實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說話,誰人來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講半天有什麼用。」 他在莫斯科就誇下海口,十五年後,中國的鋼鐵生產量要超過英國。他對出席共產黨及工人黨大會的代表們說:「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毛澤東之所以會誇下海口,其實是被赫魯雪夫激的。赫魯雪夫天性愛吹牛,十分有名。毛澤東說話之前兩個星期,赫魯雪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週年會議上,高聲喧嚷,未來十五年,蘇聯不僅要趕上、還要超越美國。毛澤東輸人不輸陣,回應「老大哥」,也要「超英趕美」。 毛澤東這麼說,其實還算謙虛。事實上,他內心有一股熊熊之火,決心超越蘇聯,要讓人人知道,尤其是要讓已經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的赫魯雪夫知道,我毛澤東也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嬰孩。他在一九五七年初對中國同志講的一席話,就有不少的辛辣和怒氣。他說:「〔蘇聯領導人〕什麼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麼?這叫不算數。看見這麼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麼共產黨員,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之故,毛澤東的新路徑充滿了中、蘇關係無可避免、日益交惡的因子。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杭州(浙江)會議和南寧(廣西)會議中,毛澤東增強對反對「倉促」和「冒進」的人士之抨擊。他再度責備這些人遵循蘇聯模式。他說:「如果我們做的每件事,都和蘇聯在十月革命之後做的事一模一樣,那我們就不會有紡織品,也不會有糧食(沒有紡織品,就沒有東西去換糧食),不會有煤、不會有電力,什麼都沒有。」他在杭州會議上改口宣稱,整風運動要貫徹到底(他自己前不久才在三中全會上決定要放鬆整風運動)。一月十八日,他在南寧警告幹部說,「反冒進」無可避免將「澆滅……六億人民的熱情」。甚且,他告訴周恩來說,周和其他幾個同志「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支持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幹部被迫要進行自我批評。日後周恩來向他的秘書解釋說,他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型態上他落在毛澤東同志之後。周恩來哀傷地說:「我必須仔細地學習毛澤東思想。」然而,毛澤東甚至提議換下周恩來,讓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出任總理。過後不久,周恩來同意下台,但毛澤東又改變心意、原諒了他。 毛澤東再度勝利。一月三十一日,他以一份重要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條〉總結兩次會議的結論,它基本上訂下大躍進的方針,提出「苦戰三年」的口號。這成為他建設中國社會主義計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於是乎,毛澤東中國特殊發展道路的概念,最先出現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後來在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間發展,而它只能在赫魯雪夫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創造的後史達林環境中才能萌生。赫魯雪夫刺激了毛澤東,不僅加速史達林化,還牴觸赫魯雪夫的意向,決定性地排斥了蘇聯的發展道路。 史達林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原先激勵著毛澤東,現在已經失去動力。結果是始於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時的史達林化時代,現在完全走到結局。從現在起,不再適合談論史達林化,應該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化。同時,我們不該忘記,在政治及意識型態領域,毛澤東只不過是中國版的史達林主義,換句話說,它是中國版的共產主義。並且,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蘇式史達林化已經終結,史達林主義作為極權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制度的影響力,在中國並無改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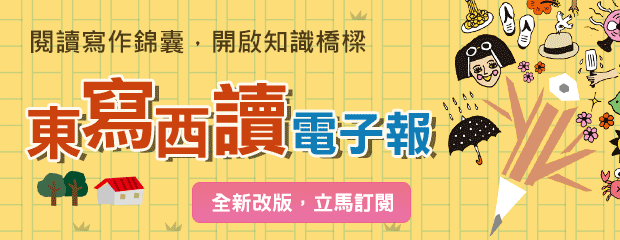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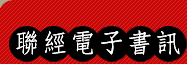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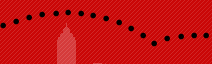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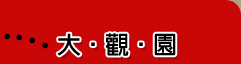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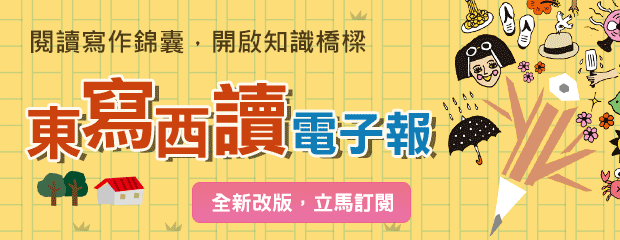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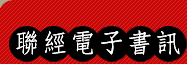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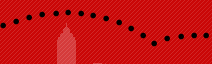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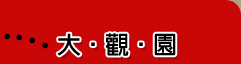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