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風之島:歷史台灣浮世繪
2012年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
2014年吳三連獎文學獎
得主林文義 一手寫詩散文小說,
一手畫筆繪出島嶼台灣
以長篇「浮世繪」呈現台灣歷史漫畫
──三百年前的海盜、荷蘭人、鄭成功、先民渡海、清法海戰、日本據台、壓制和反抗…… 浮世繪/林文義
何以長年棄筆不再作畫?識與不識的朋友讀者偶爾問起,這是我難以答覆的不安與矛盾的突兀心情,時而因此頓趕不知所措。 自我的文學書寫幾乎每年一冊的發表、合集出版循序進行,很久以前的繪事早已遙遠;卻忍不住在近年書封內頁�印上一行── 少時追隨小說、漫畫名家李費蒙(牛哥)先生習繪,早年曾出版漫畫六冊,後專注於書寫……。 每每看見這段文字,事實上是很心虛的;我疏離繪事的確很久了,一個文學作者放棄年青時代所深愛,沉迷的漫畫創作,對於彼時以莫大熱情接納有幸成為費蒙老師最後一個學生之我,是不能原諒的辜負。文學書封內頁意外地增添這麼一段和文學無關的文字,說來是向已逝多年的老師致敬亦是懺悔的表白。 青春年代的漫畫就停頓在三十六歲之前,往後直到十七年代後再應允小說家老友東年之邀,在他主舵的《歷史月刊》以台灣史借題,以一年十二期的時間(二○○四∼二○○五)逐月發表漫畫連作,落筆當下一種凜冽地心虛更深沉了。與十七年遠離的漫畫昔往彷彿是似曾相識,卻更覺不安,還能回返繪事的專注與沉穩嗎?那是一個無比寒冷的冬夜,面對空白的A4稿紙,心想退避又怕違逆了東年兄的殷切付託。 三十六歲以前那麼狂熱於借題中國古典小說,從《西遊記》、《三國演義》、《封神傳》、《七俠五義》到以台灣歷史的漫畫連作乃至於政治評論的單幅漫畫……告別繪事十七年後重拾畫筆,水準是超越或後退呢?許是由於二○○三年初在印刻出版社印行了第二部長篇小說:《藍眼睛》,秀異的小說家東年從書中讀出我依然對台灣歷史的追索念念不忘,卻要我以久疏的畫筆再次深化島國三百年的浮世繪。 我祈願此一連作是「浮世繪」而不只是尋常的「漫畫」。猶若近年的散文形態,將昔時的文字更為深化純粹一種美學,一九九○年前後曾以莫大熱情以台灣歷史作題,分別用漫畫、散文的方式出版了:《唐山渡海》、《關於一座島嶼》(台原版)起心動念在於期望下一代的讀者能初步認識從前的台灣,用心摯切。 相對以嚴謹史料為訴求的《歷史月刊》,風格想是不能過於輕漫、鬆懈的取材,縱然容許我以久疏的漫畫筆觸可以幽默呈示,我還是兢兢戰戰地決定以「浮世繪」的圖案出發。 浮世繪,源起日本。歌麿及北齋是浮世繪代表名匠,無論人物風土或山海四季皆是絕美亦是我向來傾慕的典範;我不揣淺薄地在二○○五年前後,彷彿懷抱著向大師致敬的心情,在彼時文學書寫的餘暇,回復到繪事重拾的專注。 三百年前的浪潮湧漫台灣島嶼的四方,海盜、荷蘭人、鄭成功、先民渡海、清法海戰、日本據台、壓制和反抗……。再次為我們生死以之的台灣島鄉以「浮世繪」畫幅留下歷史和記憶。這才驚覺此次,也許就是最後一次,自我竟然是以評論的觀點在質疑歷史,而不像十七年前依循著史明先生:《台灣人四百年史》、王育德先生:《苦悶的台灣》所訂下的史觀全盤接納,不論正確或偏頗,都是個人主觀看法。 其實毋寧說,浮世繪採漫畫呈現的形式依然是文學的。我以圖繪替代文字,試著為台灣再次深化顯影島鄉的從前,先民的艱辛與悲苦;繪事反而沉定而嚴肅,當然不忘漫畫本質所蘊涵地幽默與逸趣。 如同一幅幅木刻版畫的展演、虔誠之心猶若中國三○年代,豐子愷先生為魯迅的<阿Q正傳>插畫,淨身純粹地以佛經為題的《護生畫集》……。 文學書寫之餘意外的美麗。二○○五前後一方面進行短篇小說,一方面展演歷史漫畫亦試著開始習詩;無一不是文字與圖案相與並行的「浮世繪」形式,如今在天之靈的費蒙老師想必會欣慰地說──終究文學之你還是不忘繪事,這樣,很好。 內文選摘(節錄)
十二天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基隆獅球嶺砲台,發出了二十一響沉渾的砲聲,祝賀台灣民主國之誕生。 二十歲的劉阿南搬運著沉甸的砲彈,一身涔涔、黏答的熱汗。這個來自廣東梅縣的客家子弟,在與同僚搬完最後一箱砲彈之後,四肢酸痛、鬆軟地癱在砲台最左側碉堡臨海的安山岩矮牆邊,像條狗似地伸長舌頭,不停地喘氣。 「台灣民主國?大清朝廷呢?皇上不理會我們了?」 劉阿南將頸後的辮子繞到身前,不解地想著。 視野來回巡了一次,幾個同僚正拿起丈二長度的棉布桿,清理仍然冒著充滿瓦斯熱氣的砲膛,幾分鐘前的轟然巨響,如今卻只剩一片異樣的沉寂,長官說今天是大喜之日,既是大喜之日,何以發砲之後,個個一抹愁苦的臉色?那滔滔的遠海,陰茫茫一片,好像,好像什麼大事即將要發生。 就算有什麼事即將要發生,也輪不到我這微不足道的劉阿南吧?陌生的台灣島,與故鄉廣東梅縣何干?我劉阿南只不過是來混一口飯吃而已……官長前幾天匆匆來去,形色驚惶,清楚地看見他提著一只沉甸甸的布袋下山,同僚悄悄的告訴劉阿南: 「那袋裡鏗鏘作響的,是白花花的龍銀呢?」 劉阿南怔怔的張大嘴巴,好像一只圓形的燉鍋,拿掉鍋蓋般深深地「哦」了一聲,也沒再追問些什麼。 這樣的反應,其實和老母親在他遠行前的殷殷叮囑有很大的關係。劉阿南一想到在故鄉那片永遠種不出像樣歲收的貧無荒地,終日勞苦的母親,就忍不住掉淚: 「悲啊,我那年輕就守寡的老母親……」 母親緊握著劉阿南的雙手,塞給他幾個銅板兒,傷心不捨地悲泣不已。劉阿南低首,一時無措,眼角餘光不經意的瞥向門外天光白亮的大埕,曬著的梅乾菜,微酸、陳腐的霉味瀰漫在空氣中,闇暗的廳堂,祖先的牌位前剛燃上的三柱清香,像母親身上散發的味道,沉沉而古老的檀香味……「阿娘。」他低喚一聲。 「兒啊,汝知,在家鄉賺不到好吃穿,做了朝廷的兵勇,遠去台灣,聽人說,那海島自古多瘴癘,汝要小心。」 才兩個月之前的事,劉阿南同縣裡數百壯丁,參與了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的招募,抵達汕頭港,一艘船首書寫著「威靖」二字的鐵皮軍船,就這麼在春寒料峭、巨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中航行了三天兩夜,到達了台南安平,從小不曾看過海的劉阿南,在航程中起先是暈眩、昏沉,而後是將他二十年來的胃液,悉數嘔吐殆盡。 「果然,如阿娘所言,台灣是不祥之地。」 劉阿南下了船板,頭眼昏花,腳未踩穩,差點跌跤。 昏昏沉沉,異鄉一夜,醒來卻是滿眼燦麗之美景,傳說中的兩百年前國姓爺最後的「東都」,滿城蓊鬱的鳳凰樹,聽說夏至會開紅艷艷的花。 「阿南兄,這台府城果然豐盛。汝細細瞧,街坊姑娘生得真美……。」 同村自小相識的蔡阿貴嘖嘖稱奇,一雙色迷迷的眼直盯著快步逃離、驚怕的少婦,粗魯的遙指。 「在老家已娶妻房之人,切莫輕浪啊,阿貴兄。」 劉阿南笑說,一把拉著涎著臉不走的蔡阿貴,轉身往東城門行去。這是抵台翌日的休假,明天就將登上接駁之軍船,沿西部海岸前往基隆砲台。 「看府城如此,並不像家鄉父老所言,台灣是男無情,女無義,鳥不語,花不香的瘴癘之地嘛。」 劉阿南在月光皎亮的海岸兵營熄燈入眠之前,對鄰舖的蔡阿貴,有感而發地如是評論,哪知蔡阿貴早已沉沉入睡,鼾聲震天。 「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劉阿南三歲喪父,伴隨寡母,實在是窮怕了。一直到十九歲,聽聞鄉人傳誦,原籍廣東梅縣的丘逢甲高中進士,現為台灣聞人,正逢劉永福在廣東募兵,這位在清法戰役大敗敵軍的黑旗軍統領,早已是劉阿南少年心中的英雄,與其老死在貧窮的家鄉,不如投軍掙個錢,好歹混口飯吃。就這樣,劉阿南一頭栽進了即將引燃戰火的台灣。 在晨風中的練兵場,他遠遠仰望身穿紅色大斗蓬,官帽上威武流麗的翎毛隨風搖曳的劉永福,身形不高,卻雙目精亮的統領風采,劉永福朗聲訓示,緊握的右拳高高舉起,句句鏗然: 「……日寇謀台急切,我大清軍士,上承朝廷令諭,下受台民所託,誓必以命衛我疆土!」何等的氣壯山河,好個英雄劉永福。 抵達了基隆,進駐獅球嶺砲台,這才聞知,早在三月二十三日,日本軍鑑已砲擊澎湖,守軍不敵,三月二十六日僅三天交戰,日軍已登陸媽宮澳。總理大臣李鴻章於五月八日,在日本下關與日相伊藤博文竟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決定割讓台灣、澎湖。 「朝廷都割棄台灣了,護衛何用?」 兵勇們惶惶不安,私下奔相走告。劉阿南佇立在碉堡海的矮牆邊,茫惑的遙看陰沉、深邃難測的大海,總覺得有大事即將發生,逐漸不安起來的情緒日益加深,一直延續到這一天,五月二十五日。 官長命令向著大海的方位擊發二十一砲,觀測兵勇疑惑的問說: 「海域無任何敵方軍艦,何以擊發?」 「巡撫大人如今是總統之尊,今乃民主國肇始之日,全台大喜,擊砲以慶之。」 官長攤展論令一紙,照本宣科的唸了一次。 劉阿南遙望茫茫大海,忽然一陣心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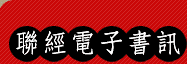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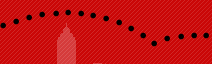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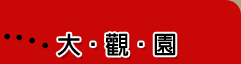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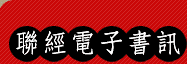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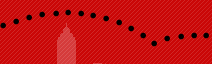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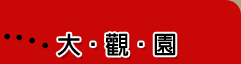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