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珊的女性唯美世界
羅蘭珊的墓
上個世紀的七O年代中,我住在巴黎第二十區,鄰近著名的拉舍斯神父(Pere-Lachaise)公墓。
巴黎最大的公墓一個是南區的蒙巴拿斯(Monpanasse),另一個就是東區建立在1804年的拉舍斯公墓。
一個城市,有過兩百年的輝煌歷史,就積累了令人驚嘆的墓地文化。看過伍迪艾倫拍攝的歐洲三部曲裡的「巴黎」,大概也就了解,對一個異國現代電影創作者而言,他心目中巴黎的「奢華」,竟然是這樣多遊走在城市夜晚街道上遲遲不肯褪去的上一世紀的魂魄。
許多人從世界各個角落到墓地尋訪他們敬愛或眷戀的魂魄,其實,不是鬼魂不願消褪逝去,是文化和美的記憶如此悠長纏綿,婉轉不去,遍布在城市各個角落吧。
墓地的樹木高大蓊鬱,是散步、沉思、靜坐的好地方。微風吹拂,花葉的芳香裡,有不容易覺察的屍體在歲月裡慢慢腐爛的氣味,有驚悚,也有領悟。
有人坐在普魯斯特倒映著天空雲朵的黑色大理石墓邊讀《追憶似水年華》,有人在皮亞芙(Edith Piaf)堆滿紅色玫瑰的墓前輕輕哼唱《玫瑰人生》裡的歌曲:
A Paris dans chaque faubourg
Le soleil de chaque journ│e
Fait en quelques destin│es
E clore un reve d'amour
每個清晨,陽光在樹隙間明滅閃耀,各人帶著各人的夢想走過。城市的這個角落,仍然傳唱著皮亞芙沙啞、彷彿老唱片變形扭曲、荒腔走板卻懾人心魄的歌聲。
如果每天在墓地散步,與兩百年的鬼魂擦肩而過,不同的時代,不同生命形式的完成,憂傷,或喜悅,意氣風發,或低鬱困頓,都已成為過去了。一個墳塚挨著一個墳塚,毗鄰而居,彷彿仍然有他們小小的愛或者恨,但是,因為都已成過去了,愛與恨,伴著淡淡花香與屍臭,隨風而逝,也都無足輕重了。
一個城市需要兩百年的愛與恨,才有了沉靜下來,懂得與鬼魂相處的寬容嗎?
2013年重回巴黎,又去了拉舍斯墓地。蕭邦的墓前總是堆滿花朵,皮亞芙也是,被音樂、歌聲安慰過,一代一代,從世界各地走來的「粉絲」,靜靜獻上一朵花。
王爾德是英語文學的主流,他的童話集、戲劇,也以各種文字在世界上流傳,「粉絲」之多,難以想像。原來石雕的墓碑,貼滿各種文字的小紙條,中文、韓文、阿拉伯文、德文、日文,遊客們揪團,留下「臉書」,幾乎毀壞了墓石雕刻。公墓管理者新想出來辦法,用壓克力透明板保護在墓碑外側,紙條就只好貼在壓克力板上,加上一個一個嘴唇紅印,密密麻麻,滿到沒有空間了,就清除一次,換上新的透明板,滿足很快就又要爆滿的鬼魂愛戀者的留言。
墓地居民的粉絲多寡,看墓前的花朵多少,就一目了然。鄧肯的墓只是骨灰盒,不像獨立墓塚,夾在像公寓一樣的小方格中,不容易找到。但還是有熱愛現代舞的死忠粉絲,在她的小方格前獻花留紙條,也有人抱怨她背叛傳統芭蕾,為何還在墓前放芭蕾舞鞋,逝者已矣,生活中的人還在計較。
也許為了避開遊客的喧譁,假日時,我偏愛走去一些安靜的墓地,像莫蒂格里安尼,像羅蘭珊。
羅蘭珊的墓,安靜樸素,尤其在上個世紀七O年代,她像是一個被藝術史遺忘的畫家。很少人談論她的創作,她的天真、單純、唯美、夢幻,好像也不適合現代美術學院喜好故作聳動誇大的論述主流,倒是世紀初詩人阿波里奈爾迷戀她的美麗,六、七年的戀愛,留下了動人的詩句,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們一同走過的巷弄,他們牽手低迴的米哈波橋(Mirabeau),他們傳奇浪漫的愛情,都因為詩句,成為城市的共同記憶,多次躺在米哈波橋上,總聽到走過的孩子隨口朗誦那些留在法語教科書裡的句子: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Et nos amours
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La joie venait toujours apr┄s la peine
塞納河流水湯湯,橋上的愛侶,手握手,眸光對望沉湎,歲月流逝,然而詩句流傳了下來,鐫刻在金屬橋欄上。
一個世代的美麗記憶,都還在橋上,活在一代一代走過的青年口中。城市沒有傳奇,不會是偉大的城市,城市沒有記憶,不會懂生命存活的價值,城市沒有愛,沒有詩句,沒有美,生活,日復一日,就只是粗鄙無意義的鬥爭。
美,看起來無關緊要,然而,或許在殘酷傷痛的現實中,美,正是生命最後唯一的救贖吧?
羅蘭珊,學院論述不關心她,她卻擁有20世紀最美麗的詩句。詩句往往比論述流傳久遠而且深廣。
我在羅蘭珊安靜無人的墓地旁,讀阿波里奈爾寫給她的詩。戰爭還沒有發生,他們在美好的時代相遇。美麗的青春,美麗的時代,美麗的城市,羅蘭珊陶醉著,她不會知道,戰爭要爆發,接下來,她要逃亡,有殘酷的現實鋪天蓋地而來,有屠殺要來,有叛國的罪名要來。現實如此粗鄙野蠻,她逃亡到西班牙,仍然畫著童話般天真美麗的故事,彷彿因為愛過、被愛過,她就相信:唯有美,可以對抗粗鄙野蠻的現實。美,是最後的救贖。
美麗的20世紀初
羅蘭珊是一位私生女,活躍政壇的父親杜雷(A. Toulet)並不認這個女兒。她從小由幫佣的母親寶琳(Pauline)單親扶養長大,也一直只使用母親的姓氏羅蘭珊(Laurencin)。
1914年六月羅蘭珊和德國男爵瓦建(BaronOttovonWa觕tjen)結婚,但也沒有依歐洲傳統更換夫姓,仍然維持母姓。這個婚姻維持六年,1921年離婚,羅蘭珊沒有子女,終其一生她保有母親姓氏。她沒有用父親姓氏,也沒有用丈夫姓氏,母親獨立自主的一生,或許影響了她,沒有依靠男性生活,在那個女性平權觀念尚不發達的時代,羅蘭珊似乎自覺要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堅持。
1902年,剛過十八歲的羅蘭珊走上藝術創作的道路,起初在美術學校學習陶瓷繪畫。傳統的手工釉料彩繪,瓷器細緻的表面,優雅、光亮、透明的色彩,細膩精緻的筆觸,羅蘭珊此後的美學風格,似乎已經在瓷器彩繪的手工裡有了最初的輪廓。
1903年,羅蘭珊認識了布拉克(G. Braque),接觸到20世紀初前衛的現代藝術,進入當時巴黎最菁英的創作者群的圈子,認識了畢卡索、德漢(Andre Derain)、馬諦斯。
1907年,畢卡索創立立體主義(Cubism),成為20世紀最革命性的藝術流派。羅蘭珊也是這個活力迸發飆揚的年輕藝術團體成員,而且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她為立體派的聚會所做裝飾設計,與前衛的年輕詩人阿波里奈爾談戀愛,一首一首為羅蘭珊創作的美麗詩篇,成為一個時代的愛情傳奇,美麗的羅蘭珊,因為詩句,因為繪畫,成為巴黎永遠的記憶。
羅蘭珊因為與創立立體派的主要健將格里思(Juan Gris),布拉克,阿波里奈爾在同一個團體,很自然會被歸納在立體派之中。在1910年前後,羅蘭珊的部分作品,像她為畢卡索畫的肖像,也的確明顯可以看到立體派切割畫面的黑色線條,以及傾向幾何形的結構。
畢卡索在1907年創作的〈阿維儂姑娘〉,被認為是立體派繪畫革命的先驅,他以銳利準確的黑色線條切割畫面,使西方繪畫的「寫實」,轉變為簡化形體的「拼接」(collage),視覺不再只是當下所見,也同時「拼接」著記憶、幻想,在畫面中,客觀真實與主觀想像的空間,像三稜鏡面,交錯、組合出新的視覺經驗。
畢卡索是雄性的、陽剛的、暴烈的、甚至霸氣的,他使立體派的畫面空間建構在極為知性的基礎上。許多幾何形狀的組織,在立體派的畫中,像數學公式的演習,不摻雜情緒,沒有愛恨,冷靜理智的黑線,像礦石的結晶切割面(cube),有稜有角,光耀閃爍,尖銳犀利。
然而羅蘭珊如此不同,她受到立體派影響,她與立體派的男性畫家如此親近,但是她似乎很知道自己女性的特質。她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唯美、溫柔、夢幻、朦朧、輕盈,她的內在美學本質,其實與立體派的主張格格不入,或者更接近當時的象徵主義和那比派(NABIS)。然而,她在前衛團體中,卻絲毫不受那些霸氣男性的影響。她只是要回來做自己,真實的自己。說自己要說的話,做自己愛作的夢,她不在意給自己的畫貼上「主義」的標籤,她不在意「潮流」,她就是她自己,在一個新世紀朦朧的曙光裡,夢想著自己像一朵花,悄悄一瓣一瓣綻放打開,含蓄而自信。
羅蘭珊的畫一直是自己私密的心事,絕不「偉大」,絕不「霸氣」,絕不宣揚什麼「主義」。她像躲在城市角落的一個孤獨的小女孩,有點迷惑,有點驚惶,看著男性的喧囂誇大,口沫橫飛的粗魯,看著戰爭與屠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經過流亡與放逐,她還是那個躲在角落的小女孩,作著她一直不願意醒來的夢。
不喜歡羅蘭珊的人會說:一輩子都在作夢,從來不看現實一眼。
是的,上個世紀末在橘園美術館,看到她為香奈兒(Channel)畫的肖像,我也曾經搖頭輕輕嘆息吧:羅蘭珊,羅蘭珊,怎麼可以這樣愛美,愛到如此至死不悔?
香奈兒在時尚名牌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女性奮鬥打拚的辛酸,她因此拒絕接受羅蘭珊把她畫得柔弱嬌媚不堪,這是一件當年被「退貨」的作品。
然而這幾年,常常數次在橘園看這張畫,我想,羅蘭珊不是在畫香奈兒,她還是在畫自己吧。她無數的自畫像是自己,她畫的其他肖像,也都是她自己。躲在一個角落的小女孩,迷惑驚惶,然而她用自己編織的夢,把自己裹起來。像一隻蠶繭裡的蛾,夢想旖旎繽紛,她不要醒來,她不願意醒來。現實這樣殘酷,她終其一生,堅持唯美,美,會不會是她生命最後的救贖?
美麗的牝鹿
早在世紀初,阿波里奈爾就曾經評論羅蘭珊美學的核心本質是──「純淨」(purity)。阿波里奈爾認為:許多女性藝術家的錯誤,在試圖超越男性,結果最終失去了自己的品味和魅力。他讚許羅蘭珊說:她深知女性與男性的不同。
阿波里奈爾當時深深迷戀羅蘭珊的美麗,她對愛人畫作的評論,或許也有盲點。羅蘭珊躋身在一群個性鮮明強烈的男性藝術家中,每個人都頭角崢嶸,每個人都自我中心,在藝術上的見解也往往誇大、獨斷、霸道。議論起來,誰也不讓誰,攻擊性極強,認為只有自己是對的,一言不合,就破口大罵,甚至扭打起來。羅蘭珊總是微笑靜靜旁觀著,一語不發。
這些占有慾、征服慾都極強烈的男性,卻都寵愛著團體裡唯一的女性,年輕、優雅、溫柔,更重要的,她如此美麗。
阿波里奈爾說羅蘭珊是「法蘭西的恩典」,這些侵略性極強的男性,圍繞著她,讚美她,歌頌她,稱她為「美麗的牝鹿」,羅蘭珊成為巴黎的一則傳奇,成為20世紀初美麗時代的一則傳奇。
羅蘭珊接受了,似乎也享受著她作為美麗女性的特權,一貫著她美學上的女性特質。是因為她的自覺,還是因為阿波里奈爾的警告?她始終沒有和男性較量的野心,沒有沾染男性獨斷的、霸氣的態度,也沒有沾染男性犀利、絕對不可妥協的黑線分割。
羅蘭珊始終保有她女性的夢幻、朦朧,她活著,在許多妥協裡活著。
她結了婚,嫁給德籍丈夫,因此自然成為德國國籍。沒有多久,德、法一開戰,她擁有的德國護照,忽然就有了「叛國罪」。羅蘭珊逃亡到西班牙,靠著藝術家朋友匹卡比亞(Picabia)幫忙,生活下來,一直到1921年才重回巴黎。
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故鄉?什麼是效忠?羅蘭珊在流亡的幾年中一定常常思考這些「男性」「國家」制定出來的規則與律法吧?她妥協了,她似乎承認自己只是一個柔弱無力的女性。她無力對抗,她只是要存活著,於是,她躲在國家之外,躲在政治之外,躲在偉大的口號之外,做一個「渺小」的女性,躲在童話裡,做兒童書本彩繪,躲在劇團裡,為狄亞基列夫舞團設計布景服裝。童話和舞台,對飽受戰爭與政治壓迫的羅蘭珊而言,似乎是更真實的現實,也更美麗吧。
1937年二戰期間,畢卡索創作了控訴戰爭暴行的史詩鉅作〈格爾尼卡〉(Guernica),然而羅蘭珊還是躲在夢幻的童話城堡裡,她創作不輟,然而終其一生,她的作品裡看不到戰爭,看不到屠殺,沒有「反映」現實。然而,什麼是真正的「現實」?她的「不看」會不會是一種拒絕,她的「不看」,會不會也可能是另一種「控訴」?
唯美,朦朧,夢幻,粉色的旖麗,繽紛的夢,她1921年離婚後,沒有再婚,收養繼女蘇珊牟侯(S. Moreau),陪伴她到1956年去世。法國還是甚少羅蘭珊的「論述」,她的畫作大量流到日本,日本為她成立了羅蘭珊美術館。
2013年法國紀念羅蘭珊誕生130年,在巴黎瑪摩丹美術館舉辦回顧展,從日本借回將近百幅羅蘭珊畫作作為展品主要內容。
羅蘭珊的魂魄,彷彿也流亡異地,她疏離在「國家」「民族」之外,疏離在「男性」歷史之外,好像安心做一名主流之外的邊緣角色。邊緣、旁觀,會不會也才使她保有了一個女性充分自主獨立的夢想的權力吧,相對於當時努力與男性創作一較長短的女性,或許,羅蘭珊彷彿反而擁有了更純粹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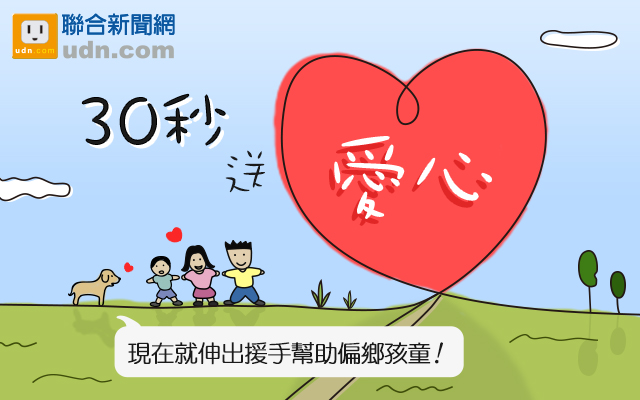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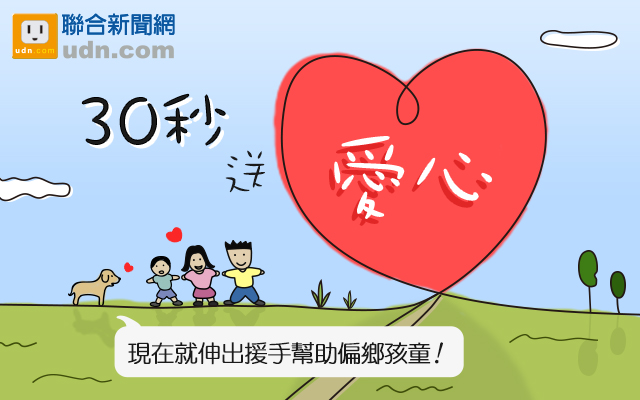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