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關鍵七問:憂思者的訪談
作者/陳宜中
今日中國,各種思想百花齊放。
本書深度訪談:
國寶級思想家錢理群,
追求社會公正與憲政民主的秦暉,
反思富強崛起、呼喚文明崛起的許紀霖,
研究底層維權抗爭的于建嶸,
非典型的毛左派袁庾華,
倡議公民儒教的新儒家陳明,
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高放。
他們各有獨到的視野,
在七篇憂思者的訪談中,
對中國的現況與未來提出不同診斷。 ******************************** 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能帶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動力,
在世界上推動人道與互助;
是不是能夠給十數億境內以及周邊社會的人民帶來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
是我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
──錢永祥,〈憂思者的思考:《中國關鍵七問》序〉 序
憂思者的思考:《中國關鍵七問》/錢永祥
當代中國充滿了難以調和的對比。它已經是世界強國之一,具備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但它既無法管束自己官員的貪腐濫權,也尚未建立人民敢信任的統治秩序。它幫助許多人在一代之間從赤貧變成富有;但從飲食、交通、住房,到教育、醫療、退休養老,幾億人民必須每天地、無奈地、心力交瘁地保護自己,鑽營機會。它的憲法明言「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不過中國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中國農民沒有農會,工農階級在黨內黨外均說不上任何領導角色和政治意義。它的體制自許「具有中國特色」,不跟隨既有的任何發展模式;不過除了維護黨國官僚集團(以及周圍的附庸)的獨占地位之外,你很難說這套體制還相信什麼、追求什麼、還有什麼理想與嚮往。 簡單言之,中國已經「崛起」,可是這個新生的龐大力量,並不清楚如何界定自己,也還在迷惘該以什麼面貌面對世界、面對自己的人民與土地。今天的中國強大到只舉得出「中國」這個符碼,其他的一切都有待摸索:這似乎是中國龐大身影所映照出的尷尬難局所在。 這種迷惘狀態,跟歷史上前一個階段適成對比。拿1900年的中國與2000年的中國對照,你約略可以看出這百年來中國發展的方向與成就。有鑑於慘痛的周折與高昂的代價,如何界定、評價這些成就與方向,各方會有嚴重的歧見;不過看來明顯的是,百年前人們認定的目標是建立現代主權國家、建立現代社會、與滿足溫飽的民生經濟。這些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主導這些工作的國共兩黨的歷史角色也告一段落。但是接下來中國要如何發展、往什麼方向發展,今天的中國人其實並沒有答案。 《思想》自許為各地華人的共同知識刊物,自然關注中國之命運,更關注中國大陸的崛起代表什麼意義。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能帶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動力,在世界上推動人道與互助;是不是能夠給十數億境內以及周邊社會的人民帶來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是我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 在當下中國,有一些知識分子與異議者也在關注同樣的問題。他們親身經歷過幾十年來的大小風暴,仍設法維持獨立的心靈,縝密的思考,寬廣的視野,以及對民間疾苦的悲憫情懷。錢理群先生選用「知我者謂我心憂」作為他一本書的題名,多少形容了這批憂思者的自我定位。陳宜中先生先後邀請了其中多位,進行訪談。受訪者對於中國當前難局的來龍去脈、對於體制的沉疴、對於中國革命史的方向與病變、對於底層抗爭與平民百姓的遭遇,皆有嚴肅、深入的理解,他們的分析與呼籲自有參考價值。而訪談的對話形式既綜合呈現受訪者的整體觀點,又能在細節處流露出他們的風格與情操,自有其吸引人處。這些訪談陸續在《思想》發表之後,引起海峽兩岸的高度矚目,在網上流傳廣遠,也激發了不少爭論。我們認為這些重要的思考結晶有必要集結成書,一則便於流傳保存,二也是為了方便讀者在各篇訪談之間對觀參照,形成自己的判斷。 身為《思想》的總編輯,我要強調陳宜中先生在這整個訪談計畫中的樞紐貢獻。作為訪談者,他必須先深入了解當前中國大陸的一般性問題;他也用心熟悉受訪者的經歷與著作,理解他們曾經提出的主張與論點;他本身更具備豐富精湛的理論與歷史素養,方能掌握整個對話的方向與結構。最重要的是,宜中扮演的始終不是一個消極的提問、記錄角色;相反,他是一位主動的對話者甚至於挑戰者,事先與受訪者磋商,界定訪談的主軸,設定議題,訪談中該追問處就追問,若是質疑、挑戰能逼出更周全的說法,那就不惜質疑、挑戰。總而言之,宜中設法讓受訪者以完整、系統的方式表達自己;他也用心設想讀者在場,幫讀者提出問題,讓讀者在閱讀時感受到訪談對話的真實與切題。 這次結集,限於篇幅,只收入了七篇訪談。但是宜中手裡尚有存稿,整個訪談計畫也會繼續進行,所以本書還將有續編。盼望這些訪談能持續地呈現與分析當下中國的重大問題,幫助中國尋找前路與遠景,讓中國的崛起不只是軍事、經濟的崛起,而能對人類做出更積極的貢獻。所謂的「大國崛起」必須提出、體現某一套普世價值:英國開創憲政與法治,法國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美國倡導民有、民治、民享,甚至蘇聯也宣揚過「無階級的社會」,彼時成為整個時代的嚮往所在,也織入了人類的共同文明史。(當然,這些大國崛起另有其黑暗的一面。)另一種強調特殊性、對抗性的崛起,如德國的「以文化對抗文明」,或是如日本的「超克現代」,則帶來了生靈塗炭、禍人禍己的後果。中國正面對歷史性的選擇,願本卷受訪者的諍言以及之後的其他訪談,能幫助中國──也幫助世界──找到理想的前進方向。 導言
中國崛起之後/陳宜中
本書收錄了七篇當代中國思想訪談,受訪者分別是錢理群、秦暉、許紀霖、于建嶸、袁庾華、陳明、高放。這七篇訪談自2009年起陸續發表於《思想》季刊,引起兩岸知識界諸多迴響與討論。因此,我們決定集結成書,期能為關切中國大陸發展的讀者(特別是台灣讀者)提供一組發人深省的中國參照。 這本訪談集以七位中國思想家及其思考為焦點,深入探問他們對中國現況與未來的不同診斷。儘管思路各不相同,受訪者在論及中國的「富強崛起」(許紀霖語)或「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錢理群語)時,皆有深刻的憂患意識。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下,這七篇「憂思者的訪談」構成一組尤具反思的中國讀本。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本是2008年北京奧運的口號,但在世人眼中,京奧的象徵意義實為中國的崛起。自美國陷入金融危機後,「中國即將統治世界」的預言、欲望或警語,更甚囂塵上。「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言猶在耳,但就在短短幾年間,大陸內部強勢興起了一波視野狹隘的國家主義浪潮,不斷吹捧「中國模式」的獨特和美妙。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展開一系列的深度訪談。 我們期盼崛起的中國大陸在自身歷史與普世價值之間找到平衡,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大國,更期待中國政權公正地對待自己的人民,尤其必須保護弱勢者,包容異議者,並且理解港澳台灣的歷史來歷,尊重這幾個社會的不同發展經驗。《思想》主編錢永祥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提到:「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能帶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動力,在世界上推動人道與互助;是不是能夠給十數億境內以及周邊社會的人民帶來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是我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這也正是本系列訪談的初衷。 七篇訪談皆經反覆提問和再三修訂而成。進行的方式是先由我根據訪談錄音逐字稿,編寫出兩萬字左右的初稿,然後追加問題,請受訪者修改補充。每一篇訪談都經過半年以上的來回討論,最終由受訪者確認後才定稿並發表。 如此耗時費神的訪談,真的有價值嗎?身為這些訪談的提問人,我想藉此機會交代幾項可能的意義。 在中國大陸,言論審查和出版管制至今仍無鬆綁跡象,因此,本書的訪談無法以完整的面貌正式在大陸出版。《思想》提供了一個暢所欲言的園地,這本身正是一種言論自由的實踐。 訪談過程中,我也提醒受訪者,他們不只是對大陸讀者發言,更務必考量台灣讀者及其可能的質疑。在編輯過程中,我做了適度「翻譯」,盡量使用台灣讀者較熟悉的文字。 身為主要的提問人和訪談的編修者,我很自然而然地、也無可避免地帶有台灣的印記。在反覆的提問中,某種「台灣因素」無所不在。所謂「台灣因素」,簡單的說,就是從台灣的現實生活經驗出發,對於中國大陸有所關切與介入,也對它提出期盼與要求。由於事實上兩岸的人民休戚與共,歷史相互滲透,命運相互影響,我們不能不做為「參與者」(而非旁觀者)主動、正面地介入大陸知識界有關中國走向的論辯。本書的七篇訪談正是對話的起步,希望不只提供了思想對接的橋樑,還能有「共促進步」的觸媒作用。 各篇訪談概要
錢理群先生是這個系列訪談中第一位受訪者。錢先生在北大執教期間,以魯迅和周作人研究著稱。2002年退休後,接連出版《拒絕遺忘》、《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等民間思想史鉅著。他在訪談中指出,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走的就是「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中共建政後,先後經歷了三種不同的一黨專政模式,但始終邁不過一黨專政這一門檻;今日中國的兩極分化、生態破壞、精神倫理危機等,終須歸結於一黨專制和國家主義。此外,他強調魯迅的「立人」思想和國民性批判的當代意義:「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以立人為中心,要更關注人的個體生命的成長、自由、發展。」「只要中國人心不變、國民性不變,再好的制度到中國來,也仍然行不通。」他呼籲大陸知識分子積極爭取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在制度重建之外,還需要全面的文化重建、價值重建和生活重建。 早年,錢先生曾是文革的全程參與者,是造反到底的造反派。他後來對毛主義的反思批判,都同時也指向他自己。魯迅是他最主要的思想和精神資源,他立志繼承「魯迅的五四」,做為永遠站在平民一邊的「魯迅左翼」。在今日大陸的左右光譜上,錢先生是一位難以歸類的國寶級思想家。 秦暉先生也曾是文革期間的造反派。在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爭中,他是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在自由主義陣營中,他是最早提出「大分家中的公正問題」的論者,對鄧小平南巡後的「權貴私有化」持堅定的批判立場。按他的陳述,南巡後的經濟改革是一種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一種專制分家;在俄羅斯,正因為此種分家方式太不公正,引發寡頭派和民粹派的惡鬥,也才使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為可能。不公正的專制分家,為中國未來種下了危險因子。如果不想付出推倒重來的社會代價,高稅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作為矯正正義)也就無可迴避。 秦先生強調,贊成福利國家,須以這個國家是民主國家作為前提。民主福利國家的二次分配,關乎社會公正與公民基本權利。俾斯麥式威權體制下的福利,只是皇恩浩蕩而已;在當前中國的專制體制下,福利更經常淪為一種負福利。因此,他闡發以「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作為憲政左派與憲政右派的共同底線。他申論:如果左派不為政府擴權,而是積極追問其責任;如果右派不為政府卸責,而是努力制約其權力;那麼,中國就會逐漸趨近於權責相符的憲政民主。 許紀霖先生把晚近的中國崛起界定為一種「富強的崛起」。在他看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僅實現了富強的崛起,還沒有實現「文明的崛起」。受到富強崛起的鼓舞,大陸出現了一波鬼鬼祟祟的國家主義政治神學。和昔日的德日法西斯相似,這是一種只有明確的反抗客體(即「西方」)卻沒有主體的抵抗。如果這類國家主義繼續與集權體制、與法家的富國強兵同流合污,恐將把民族拖向無底深淵。唯有當國家理性受到現代啟蒙理性的制約,並與儒家的人文傳統相結合,中國才可望實現文明的崛起,成為普世文明的領航者。 許先生不諱言,以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大國地位,它勢將崛起為對周邊具支配力的帝國,而不僅是另一個民族國家而已。但徒具支配力的強權並不可欲,唯有引領普世文明的大國才能得到全球尊重。他指出,當前富強崛起的中國,只是一個自利性的、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社會,再加上政治上的威權主義。在此種霍布斯式的秩序下,沒有宗教,沒有道德,更沒有社會。中國之亂已經不是亂在表層,而是亂在心靈。沉疴已久,制度改革將只是治標的止血;當前中國危機是整體性的,非得從基礎上重建社會、重建倫理不可。在此,他多方面呼應了錢理群先生的憂慮。 于建嶸先生長期研究底層中國的維權抗爭,首創「剛性穩定」概念以界定維穩體制。近年來,由於他的「敢言」及其所依據的實證調查,他成為大陸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出於《思想》的訪談要求,于先生首度較為系統性地交代了他的學思歷程和基本理念。他從幼年經驗談起,解釋他為何主張「個人權利至高無上,社會得先保護個人的權利才會有公共的利益。」他對中國當前的農民和工人抗爭,農會和工會問題,各種「群體性事件」及其動力等,有一套獨特的分類和理解。 于先生指出,中共的核心考量並不是經濟發展,而是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基於此,大陸的穩定主要是以「是否影響共產黨的政權穩定」為標準,這跟今日台灣非常不同。中共為了鞏固政權,把一切可以疏導壓力的管道都視為不穩定因素,這正是「剛性維穩」體制日新月異的根本原因。然而,他並不認為中共絕無可能改變,只是中共不會因為「理念」而改變,只會在強大的政治社會「壓力」下改變。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革,他持審慎的樂觀:「大陸會逐漸走向台灣的政治運作邏輯。」 在今日大陸的毛派或「毛左派」中,袁庾華先生是一位相當特殊的人物。初中後,他就到鄭州肉聯廠當工人,爾後成為河南省造反派的骨幹。1995年後,他參與鄭州沙龍的創建和經營。在訪談過程中,袁先生除了回顧他的造反派經歷外,亦對毛澤東和毛時代多所肯定。然而,他幾項主要的政治主張,卻與主流的毛左派有所差異。當前以「烏有之鄉」作為主要代表的大陸毛左派,尚未接受他「結合程序民主(含競爭的政黨政治)和大民主」的倡議。他呼籲中國政府同時平反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和法輪功成員,並強調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是全世界底層人民奮鬥出來的成果,一定要在中國實現。但時至今日,多數大陸左派仍視如此主張為漢奸「引狼入室」的詭計。 訪談中,我屢次打斷袁先生,詢問他的見解是否為今日大陸毛左派的主流意見,並請他闡發程序民主和大民主之不同,以及他何以主張兩者應相互結合。他表示,他的民主思路與大陸底層毛派群眾是相通的,只是部分毛左派尚未充分體認到結合程序民主之必要。值得一提的是,袁先生訪談在《思想》發表後,通過大陸網站的轉載,在毛左派內部引發了激烈的政治論辯。 1980年代初,牟宗三先生曾力主「第五個現代化」,要求台灣當局推動民主轉型。但在今日大陸,呼喚民主轉型的新儒家幾不可得。在大陸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中,陳明先生屬於對自由民主有較多同情的一位。他在訪談中指出,台灣儒家之不談「儒教」,是因為儒教在台灣的教化力量太大,所以不必這麼談。在大陸,儒門淡薄,社會基礎薄弱,因此,大陸新儒家提倡儒教作為一種宗教。但他反對蔣慶、康曉光等論者「立儒教為國教」的政教合一路線。他主張儒教在另外兩個方面進行努力:一是發展「作為一個宗教的儒教」,為儒教徒提供更充實的生死靈魂論述;第二,要立志把儒教建構為「公民宗教」,為中華國族提供跨族群的認同鋪墊。 陳先生表示,他不是文化民族論者或文化國家論者,也不是天下主義者。對外,他看重中國作為國際現實下的一個利益主體。對內,他認為在中華國族的構建過程中,儒教爭取「公民宗教」的功能和地位是可能的,甚至必要。「公民儒教」如何與憲政民主的權利意識接軌,是他現階段的努力目標。 在這本訪談集中,最資深的受訪者是高放先生。他出生於同盟會家庭,1946年入北大政治系後,轉向了中共。1950年起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受推崇為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首席專家。文革後,他率先對「個人崇拜」提出批判,並於1988年擔任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91年蘇聯解體後,他更不斷呼籲中共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 高先生在訪談中表示,他不認為多黨平等競爭目前是可行的,因為中共絕不會接受。按中國憲法,省長需由民選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故而,只要把憲法理順,黨政分開,中國就可以邁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現階段尚不需要考慮到黨外,但要讓民主黨派壯大,要實施共產黨內的差額競選。他指出:當前的「中國模式」是四不像,唯有清理掉兩極分化的美國模式成分、嚴控思想言論的蘇聯模式成分、國營壟斷的歐盟模式成分,才能真正實現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謝詞
最後,我特別要感謝聯經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和《思想》主編錢永祥先生。沒有他們長期的支持鼓勵,這些訪談不可能問世。也謹此向聯經的副總編輯胡金倫先生致謝。
在形成這七篇訪談的歷程中,多位台灣年輕朋友協助整理訪談錄音,另有二十幾位大陸朋友慷慨地提供建議和支援,謹在此一併致謝。 非常感激受訪的大陸前輩不厭其煩地容忍我不斷的提問和編輯要求,謹以此書向他們致敬。 內文選摘(節錄)
崛起中國的十字路口:許紀霖訪談錄
許紀霖先生,浙江紹興人,1957年出生於上海。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1977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受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影響,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反思,以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的研究。從「啟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國思想界的分化,並積極介入當代論爭,為大陸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寫有《無窮的困惑》、《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化史》(主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著作。 一、1980年代的啟蒙及其分裂
王超華(以下簡稱「王」):許先生,可否請您先談談您的成長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屆的? 許紀霖(以下簡稱「許」):我1957年出生,在上海長大。文革時我是小學生,紅小兵。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在上海市郊的東海農場。1978年作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我本科4年畢業後,剛好缺青年教師,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間在職讀碩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時,歲數算是比較小的。 許:我們班上,幾乎全都是「老三屆」,所以我是小字輩。班長與班裡年齡最小的相差15歲,他開玩笑地對他說:「我都可以把你生出來了。」我自己觀察,老三屆的話題總是繞不過文革。關於文革,有三個不同的年齡層,區別在於康有為所說的「所經之事」、「所見之事」和「所聞之事」。對老三屆,文革是「所經之事」。對我這個紅小兵而言是「所見之事」,因為我沒有直接經歷,就算經歷也是很間接的。而對文革後的一代,文革則是「所聞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學的時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鄉雖然經歷過,但畢竟經歷有限,沒有很直接的心理衝撞。我覺得跟老三屆相比,自己與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親和性。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您最初做的是民主黨派研究,大學時代就對這題目感興趣? 許:純屬偶然。念大學時,自己亂看書。畢業留校之後,系裡要我跟著一個老師研究中國民主黨派。我對民主黨派本身沒什麼興趣,但發現那些民主黨派人士不得了,個個都是大知識分子;他們在20世紀前半葉的命運,與當代知識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內心之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我的第一篇稿,寫的是黃遠生。他是民國初年的名記者,袁世凱稱帝時要他幫忙造勢。他非常掙扎,寫完了又很後悔,因此後來寫了《懺悔錄》,懺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寫了一篇〈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王焱是《讀書》的編輯部主任,竟然把我這個無名之輩的處女作發了出來,給我很大的鼓勵。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我寫了二、三十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個案我稱之為「心態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態史研究」提升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從個案出發,提煉出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就像以賽亞•柏林和別爾嘉耶夫對俄國知識分子的研究。 王:您為何認為大學的經歷是最重要的? 許:1980年代大學的氛圍,與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私人空間很少,連談戀愛都很拘束,與女同學稍為接觸多一點,支部書記就會來干預。但1980年代校園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躍:競選人大代表、模擬審判、討論國家大事、上街遊行等等,熱鬧極了。1980年代有一種後文革的氛圍,文革中的紅衛兵精神轉化為一種「後理想主義」,從「奉旨造反」轉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開放。1980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大視野、大思路、大氣魄,這種精神對我影響很深。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父與子兩代人。父親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比如赫爾岑、屠格涅夫,既有懷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內涵而沒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動猶豫。兒子一代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的信念很簡單,為一個簡單的主義奮鬥,非常有行動力;但他們有力量而沒有內涵,堅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當代中國兩代知識分子似乎剛好倒過來。像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輕信而行動力強;我們都是行動主義者,總是要有一個信念,都喜歡大問題,具有實踐性,而這恐怕都與文革的紅衛兵精神有關。而1990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比如我的學生一代,書讀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國父親那代,常常有一種無力感;他們在虛無主義的環境中生長,經常懷疑行動的功效與意義,成為遊移不定的「多餘的人」。 陳:您怎麼看1980年代跟文革的關係? 許:像我們這些1980年代人,總是從大處著眼,總是在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大問題,胸懷責任感,而且有所行動。如果我們把毛澤東時代看作一種紅色宗教,類似革命烏托邦的宗教時代,具有一種神聖性,那麼1980年代不過是這神聖性的世俗版。1980年代去掉了毛的神聖性,但重新賦予啟蒙、現代化以某種神魅性。中國真正的世俗化要到1990年代之後才完全展開。在中國,1960-70年代生的人還多少受到1980年代的精神洗禮;但「80後」一代則完全在1990年代之後的世俗化環境下成長起來,在文化性格上是全新的一代人,與1980年代開始格格不入。這個新,一個是世俗化,另一個就是虛無主義。 陳:您如何看待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以及1990年代以後的變化? 許:傅柯講過,啟蒙是一種態度。1980年代的啟蒙,按照汪暉對五四運動的說法,擁有「態度的同一性」。在1980年代,大家對現代性的想像是同一的,這可以用帕森斯關於現代性的三條鐵律來形容:個人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這就是新的現代性烏托邦,1980年代的啟蒙陣營是建立在這種共同的現代性想像基礎上的。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思想界,可以分為1980年代、1990年代與2000年以來三個階段。1980年代是「啟蒙時代」;1990年代是「啟蒙後時代」,即所謂later enlightenment;2000年以來則是「後啟蒙時代」,這個「後」是post的意思。1980年代之所以是啟蒙時代,乃是有兩場運動: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與中後期的「文化熱」,現在被理解為繼五四以後的「新啟蒙運動」。新啟蒙運動與五四一樣,謳歌人的理性,高揚人的解放,激烈地批判傳統,擁抱西方的現代性。它具備啟蒙時代一切的特徵,充滿著激情、理想與理性,當然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緊張性。 到1990年代,進入了「啟蒙後時代」,或者叫「啟蒙後期」。1980年代啟蒙陣營所形成的「態度的同一性」,在市場社會出現之後,逐漸發生了分化,分裂為各種各樣的「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新左派等等。啟蒙是一個文化現象,最初是非政治的;啟蒙運動的內部混沌一片,包含各種主義的元素。歐洲的啟蒙運動發生在18世紀,也是到19世紀經濟高速增長、階級分化的時候,出現了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化。不過,1990年代的許多基本命題依然是啟蒙的延續,依然是一個「啟蒙後時代」。 2000年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之所以稱之為「後啟蒙時代」,這個post的意思是說:在很多人看來啟蒙已經過時了,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 陳:關於啟蒙,在六四之前,就已經有了不同的意見,像是李澤厚等人認為不需要再談啟蒙了,但王元化仍主張要談。 許:1989年王元化先生談啟蒙的變與不變,所針對的是林毓生先生。那時林先生已經看到了啟蒙的負面,但國內學者還是認為啟蒙是好的。當時他們不贊成林毓生對全盤反傳統的分析。一直到1990年代初以後,大家才開始反思,才注意到啟蒙的負面性。這反思是跟六四有關係的。 陳:林毓生先生所講的創造性轉化,今天有不少人覺得太西化了。但在1980年代,他的觀點卻被認為是太反啟蒙、太反五四、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太友善。您如何理解這個反差? 許: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那些高調反傳統的,對傳統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通過批傳統來批現實中的政治專制主義,就像文革時「批林批孔」也是借批孔而打林一樣。但1980年代老一輩的中國文化書院派,像湯一介、龐樸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有同情性了解的。他們是一批釋古派,通過重新解釋傳統,將傳統與現代化結合起來。他們成為1990年代初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先聲。 儘管1990年代出現了文化保守主義,但他們仍在啟蒙陣營的裡面。他們追求現代性這點是不變的,只是要為普遍現代性在中國找到它的特殊表現,即以儒家為代表的、具有中國特殊性的現代性道路。19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承認普世現代性的;這與近10年出現的以狂批普遍主義為前提的「中國模式」論、「中國道路」論、「中國特殊」論是很不一樣的。 1990年代的保守主義是溫和的,基本是文化保守主義。余英時認為儒教分兩部分:政治儒教已經不適應民主政治,過時了;但心性儒家還有其存在的意義。1990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義是想把心性儒家與民主政治接軌,即從「老內聖」開出「新外王」。 然而,新儒家中的蔣慶是個極端的個案。他從一開始感興趣的就是政治儒學,不是心性修養的宋明理學,而是漢代董仲舒那套政治意識型態。而且還像康有為那樣,企圖以儒教立國,要通過國家的行政力量,將讀經列入學校的必修課程。至於出版經書的巨額利潤,都要歸他領導的儒教學會!他是文化保守主義轉化為政治保守主義的一個例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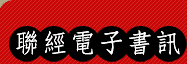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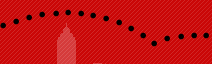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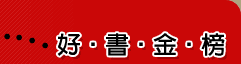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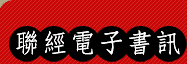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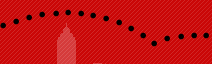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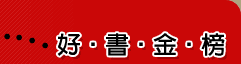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